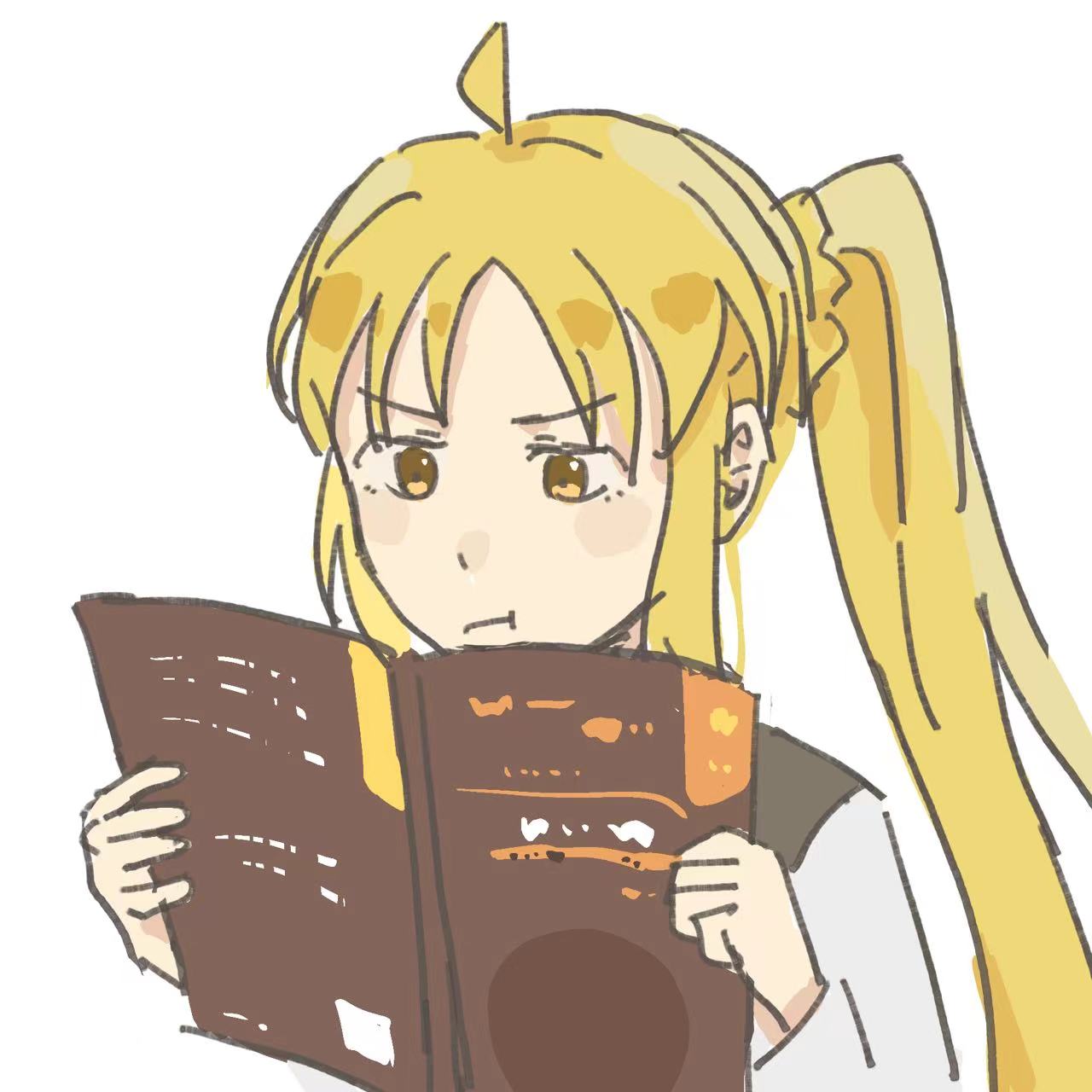本科阶段在振幅社区对丛代数有所耳闻,最近心血来潮想稍微看点这方面的科普,正好发现我导师以前写过一篇介绍文献,一拍即合!以下节选「数理科学」杂志2015年3月号「団代数をめぐって」中三篇文章的翻译,用于本人练习日语科技文献阅读。
声明:此内容仅供学习交流使用,严禁用于商业用途,使用者请在下载后的24小时内删除。本内容使用AI辅助翻译,虽然本人已尽力校对,但并不保证内容的绝对正确性。
什么是丛代数 [中西 知樹]
这是卷首文章的翻译,原文名「団代数とは何か」。
本特集的主题——丛代数(cluster algebra),是由Fomin与Zelevinsky在2000年左右提出的一类交换代数结构。丛代数具有一组称为丛变量的特殊生成元,这些生成元通过一种称为“突变(mutation)”的关系式(或递推关系)相互关联,这是其显著特征。这一概念着眼于李理论中多种代数与组合结构(例如Grassmannian的Plücker坐标、李群坐标环中的关系式)所共有的“Laurent性”,对其进行了统一与推广。丛代数最初提出的动机,可以认为是希望藉此对李群和量子群中的组合结构与现象获得更全面的理解。
最早注意到丛代数的是表示论领域的研究者。他们敏锐地观察到丛代数中的“突变”与代数表示论中Auslander-Reiten理论所出现的“突变”之间存在深刻的相似性。这一发现最终促使Buan、Marsh、Reineke、Reiten和Todorov等人于2004年左右为ADE型的丛代数提供了基于代数表示的范畴化(categorification)。以此为开端,表示论与丛代数这两个领域相互关联、相互推动,实现了飞跃性的发展,直至今日仍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另一方面,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在00年代前期,Gekhtman、Shapiro和Vainshtein从离散动力系统的泊松结构的视角,而Fock与Goncharov则从Teichmüller理论的视角,分别在一定程度上受到Fomin和Zelevinsky工作的影响,但又本质独立地抵达了丛代数中“突变”的概念。
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至少直到00年代末(除一部分代数表示论研究者外),几乎未受到这一潮流的影响。就笔者个人而言,最初认识到丛代数是2008年3月参加在伯克利的数学科学研究所(MSRI)举行的李理论研讨会时的事情。当时,约有5场报告的标题中含有“cluster algebra”,初看议程时笔者还曾疑惑“丛代数究竟为何物”。然而,在听了研讨会开头Fomin所作的主旨演讲后,我立刻意识到这本质上与我自90年代起一直研究的可积系统中所出现的T-系和Y-系等代数关系式是同一事物。以此为契机,笔者开始了对丛代数及其应用的研究,并持续至今。
事实上,我开启丛代数研究的这一契机似乎并非个例。2008年12月,在墨西哥参加我人生中第一场以丛代数为主题的研究会时,我曾向当时已发表多篇丛代数论文的Jan Schröer先生自我介绍说“I am a newcomer in cluster algebras.”,并讲述了上述经历。他听后回答道:“Oh, I had exactly the same experience.”,并接着说“Everyone is a newcomer!”,这番话让我顿感轻松,至今记忆犹新。也就是说(至少在当时),并不存在一开始就是丛代数专家的人,大家无不是从各自的研究领域走来,带着“这类现象我见过”或“这东西我早就熟悉”的认识,汇聚到丛代数这一领域中来。
这样写来,或许会让人误以为Fomin和Zelevinsky的成果仅仅是为众人已知的某种代数与组合结构起了个新名字,但事实绝非如此。正是他们将这些内容识别为一种名为“丛代数”的、具有共性的特殊结构,并为之建立了系统的理论和工具,才使得许多以往难以攻克的问题得以解决,推动了我们认知的边界,引领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言归正传。接下来,必须就本文标题所点明的主旨——“丛代数是什么”——展开论述了。当然,数学中这类“~~是什么?”的问题,其答案通常因视角不同而具有多重层次,并不存在一个唯一、封闭的解答。即便如此,若被问及自己所认定的专业领域内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从自身立场出发,总还是应该给出一个初步的回答。因此,在强烈声明以下仅为个人见解的前提下,请允许我阐述当前的想法。
丛代数自引入以来已近15年,它与众多数学分支的多样化关联已被大量揭示。时至今日,认为丛代数是数学各领域中普遍存在的一个基础的(underlying)代数与组合结构,这一认识应无太大争议。然而,将此作为“丛代数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答案,未免有些抽象。不过,(虽然这样推进话题略显强硬!)这种丛代数的普遍性(ubiquity),不禁让人联想到另一种同样是代数与组合结构的“根系(root system)(或Coxeter群)”。而实际上,我(以及我周围的一些同仁)认为,丛代数理论是根系理论的一种扩展。例如:
- 丛代数中的核心概念——突变,是具有对合性1的,这可视为根系中镜反射的有理函数版本。
- 而突变的热带化版本,则可视为镜反射的分段线性版本。
遗憾的是,这一观点目前仍未成熟,尚未达到能将丛代数理论具体地、系统性地表述为根系扩展理论的阶段。但是,作为所谓的“第零近似”,将丛代数理论视为根系理论的扩展来审视,至少在现阶段,我认为是一个良好的立足点。
最后,关于“cluster”一词。它本是一个普通英语单词,但在日本,其作为技术术语的含义(如“聚类分析”)更为人熟知,其本意反而不一定广为人知,因此在此稍作说明。查阅《牛津英语词典》,该词释义为:“1. a group of things of the same type that grow or appear close together;2. a group of people, animals or things close togather”。换言之,它意指“同种类的人或物紧密相邻的状态”,根据具体对象和规模可译为“群”、“丛”、“集”、“団”2等。例如:a cluster of spectators(一群观众)、a cluster of buildings(一片建筑群)、a cluster of tourists(一队游客)。2008年春天,我与伊山修先生在我们常去的中餐馆里商讨“cluster algebra”的译法,考虑到“群”和“集”在数学中已有其他特定含义,便认为“団代数”或许是更合适的选择。本特集的标题也采用了这一译名,但需要说明的是,各篇文章中的具体译法由执笔人自行决定。顺便一提,若在谷歌上搜索“クラスター”3,会出现“环境纳米集群”、“食品集群”、“健康医疗集群”4等许多含义不明的词组,这些其实是日本中央政府部门下属机构的事业项目名称。
丛代数入门 [中西 知樹]
这是杂志第一篇文章的翻译,原文名「団代数ことはじめ」。 本文是面向初次学习丛代数 (cluster algebra) 读者的入门篇。
1. 第一步!
首先,让我们尝试进行以下计算(拿起铅笔,一起来吧!)。
我们从两个变量 $x_1(0), x_2(0)$ 开始。这里的 0 表示时间 $t = 0$ 时的变量。假设时间是离散前进的,时刻 $t = 1$ 的变量 $x_1(1), x_2(1)$ 的演化规则由关系式
\[\begin{aligned} x_1(1) &= (x_2(0) + 1)/x_1(0), \\ x_2(1) &= x_2(0) \end{aligned}\tag{1}\]定义。为简便起见,下面我们将“初始变量” $x_1(0), x_2(0)$ 记作 $x_1, x_2$。
接着,时刻 $t = 2$ 的变量 $x_1(2), x_2(2)$ 的演化规则,通过交换两个变量的角色,定义为:
\[\begin{aligned} x_1(2) &= x_1(1), \\ x_2(2) &= (x_1(1) + 1)/x_2(1) \end{aligned}\tag{2}\]这里,将 $x_1(2), x_2(2)$ 用初始变量 $x_1, x_2$ 表示(一起来!):
\[\begin{aligned} x_1(2) &= x_1(1) = (x_2 + 1)/x_1, \\ x_2(2) &= (x_1(1) + 1)/x_2(1) \\ &= ((x_2 + 1)/x_1 + 1)/x_2 \\ &= (x_1 + x_2 + 1)/x_1x_2 \end{aligned}\]以下,我们决定交替重复使用变量演化规则。然后,尝试将依次得到的变量 $x_1(t), x_2(t)$ 表示为初始变量 $x_1, x_2$ 的有理式。例如(从这里开始的计算是关键!):
\[\begin{aligned} x_1(3) &= (x_2(2) + 1)/x_1(2) \\ &= \frac{(x_1 + x_2 + 1)/x_1x_2 + 1}{(x_2 + 1)/x_1} \\ &= \frac{(x_1x_2 + x_1 + x_2 + 1)/x_1x_2}{(x_2 + 1)/x_1} \\ &= (x_1 + 1)/x_2. \end{aligned}\]这里请注意,在最后的等式中,由于分子可因式分解 $(x_1x_2 + x_1 + x_2 + 1) = (x_1 + 1)(x_2 + 1)$,因子 $x_2 + 1$ 被约去,得到了非常简化的结果。另一方面,
\[x_2(3) = x_2(2) = (x_1 + x_2 + 1)/x_1x_2\]再继续下去(就差一点了!):
\[\begin{aligned} x_1(4) &= x_1(3) = (x_1 + 1)/x_2, \\ x_2(4) &= (x_1(3) + 1)/x_2(3) \\ &= \frac{(x_1 + 1)/x_2 + 1}{(x_1 + x_2 + 1)/x_1x_2} \\ &= \frac{(x_1 + x_2 + 1)/x_2}{(x_1 + x_2 + 1)/x_1x_2} = x_1. \end{aligned}\]这里也是,由于分母和分子的约分,结果变得简单了。最后再进行一次时间演化,分母和分子再次发生约分,
\[\begin{aligned} x_1(5) &= (x_2(4) + 1)/x_1(4) \\ &= \frac{x_1 + 1}{(x_1 + 1)/x_2} = x_2, \\ x_2(5) &= x_2(4) = x_1, \end{aligned}\tag{3}\]于是得到
\[\begin{aligned} x_1(5) &= x_2(0), \\ x_2(5) &= x_1(0) \end{aligned}\]结果表明,变量交换顺序后回到了初始变量。也就是说,我们明白了这个时间演化规则具有半周期 5 的性质。
实际上,这个计算不是别的,正是最简单的非平凡丛代数——$A_2$ 型丛代数中丛变量的突变计算。并且,这个虽然基础但充满神秘的计算,蕴含了丛代数的精髓。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引入一些丛代数的术语。将每个时刻 $t$ 的变量组 $(x_1(t), x_2(t))$ 称为丛 (cluster),各自的变量 $x_1(t)$,$x_2(t)$ 称为丛变量 (cluster variable)。特别地,将时刻 $t = 0$ 时的丛变量 $x_1, x_2$ 称为初始丛变量 (initial cluster variable)。此外,将丛的时间演化 $(x_1(t), x_2(t)) \mapsto (x_1(t+1), x_2(t+1))$ 称为丛的突变 (mutation)。
那么,让我们回顾一下上面的计算。
(i) 突变的对合性。 在上面的计算中,我们交替进行了两种变换 (1) 和 (2) 作为丛的突变。例如,如果连续进行相同的变换 (1),则有
\[\begin{aligned} x_1(2) &= (x_2(1)+1)/x_1(1) \\ &= \frac{x_2+1}{(x_2+1)/x_1} = x_1, \\ x_2(2) &= x_2(1) = x_2, \end{aligned}\]即连续进行两次变换 (1) 会得到恒等映射。这被称为突变的对合性 (involutiveness)。
(ii) Laurent 性。 通常,在多变量的既约有理式中,分母为单项式的式子称为 Laurent 多项式。例如,
\[\frac{x_1+x_2+1}{x_1x_2}\]是关于 $x_1, x_2$ 的一个 Laurent 多项式。现在,变换 (1) 和 (2) 是有理变换(由有理式定义的变换),因此对于任意的 $t$,$x_1(t)$,$x_2(t)$ 显然是初始丛变量 $x_1, x_2$ 的有理式。然而,实际上由于分子分母总是发生了非平凡的约分,使得 $x_1(t)$,$x_2(t)$都成为了 $x_1$,$x_2$ 的 Laurent 多项式。这被称为丛变量的 Laurent 性(Laurent property)。
(iii) 分母向量与根的关系。 仔细观察会发现,除了初始丛变量 $x_1, x_2$ 之外,丛变量恰好只有以下 3 个 Laurent 多项式:
\[\frac{x_2 + 1}{x_1}, \quad \frac{x_1 + 1}{x_2}, \quad \frac{x_1 + x_2 + 1}{x_1 x_2} \tag{4}\]将这些 Laurent 多项式的分母中出现的单项式 $x_1, x_2, x_1 x_2$ 的幂次5与向量 $\alpha_1, \alpha_2, \alpha_1 + \alpha_2$ 等同看待,并将其称为分母向量(denominator vector)。这些分母向量与 $A_2$ 型根系的正根 (positive roots) 一一对应。
(iv) 正性。 除了初始丛变量外,出现的丛变量中的 3 个 Laurent 多项式 (4) 的分子都是正系数的多项式。这个事实称为丛变量的正性(positivity)。变换 (1) 和 (2) 本身虽然是正系数的有理式,但正性是一个非平凡的结果。这是因为,通过正系数有理式的分子分母约分得到的既约有理式不一定总是正系数的。例如,
\[\frac{x_1^3 + x_2^3}{x_1 + x_2} = x_1^2 - x_1 x_2 + x_2^2\](v) 有限性。 丛变量的周期性 (3) 也是一个值得特书的结果。这种周期性与五边形有关,有时被称为五角恒等式 (pentagon identity)。由这个周期性可知,即使此后无限地重复时间演化,也只会出现有限个丛变量,这得到了有限性 (finiteness)。
这些结果本身,究竟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积累,尚不明确。然而,Fomin 和 Zelevinsky 洞察到这类结果的背后存在着某种代数的、组合的构造,并将其作为丛代数进行了形式化。
供参考,我们将 Fomin、Zelevinsky 以及 Berenstein 关于丛代数的一系列基础论文的列表 6 列于文末。此外,关于丛代数的文献等各种信息,可以在由 Fomin 本人编辑的网站 “Cluster Algebras Portal” 上获取。
2. 箭图及其突变
作为丛代数“入门知识”中接下来需要了解的,是一种被称为“箭图(quiver)突变”的东西。让我们来说明一下。
将由顶点集合及它们之间的箭头集合构成的有向图称为箭图(quiver)。假设箭图的顶点标有编号 $1, …, n$。例如,下面给出的是箭图的一个简单例子。

在箭图中,将起点和终点相同的箭头称为环(loop),此外,对于不同的顶点$ i$,$j$,将由从$ i $指向 $j $的箭头和其反向箭头组成的配对称为 2-圈(2-cycle)。

定义: 对于没有环和 2-圈的箭图 $Q $及其顶点$ k$,将通过以下操作得到的、新的没有环和 2-圈的箭图$ Q’$ 称为在顶点 $k$ 处 $Q$ 的突变(mutation),记作 $Q’ = μ_k(Q)$: (步骤 1)对于任意两个与 $k $不同的顶点$ i$,$ j$,假设存在$ p $个从 $i $指向 $k$ 的箭头,$q $个从 $k $指向$ j $的箭头,则在$ Q $中添加 $pq $个从$ i $指向 $j $的箭头。 (步骤 2)将所有与 $k $相连(进入或离开 $k$)的箭头的方向反转。 (步骤 3)尽可能多地移除在步骤 1 中产生的 2-圈。
例如,对于前面所举例中右侧的箭图,在顶点 1 处的突变如下图所示。

通常,容易验证箭图的突变具有对合性(involutive),即 $μ_k(μ_k(Q)) = Q$。
稍微离题一下,在丛代数的范畴化理论等领域也非常著名的 Bernhard Keller 先生,提供了一个用于在计算机上执行箭图突变的应用程序,名为 Quiver Mutation。这是一个简单但功能非常强大的免费应用。这个程序不仅能进行箭图突变,还能执行丛代数的各种运算(其中许多用手工进行是很困难的),因此可以说是丛代数研究者的必备工具。
现在,对于一个没有环和 2-圈且具有$n $个顶点的箭图 $Q$,可以定义一个$ n $阶反对称(整数)矩阵 $B = (b_{ij})_{i,j=1}^n$,其定义如下:
\[b_{ij} = (\text{从顶点 } i \text{ 指向顶点 } j \text{ 的箭头数量}) - (\text{从顶点 } j \text{ 指向顶点 } i \text{ 的箭头数量})\](以下,矩阵均指整数矩阵)。反之,对于一个 $n$ 阶反称矩阵 $B$,考虑 $n$ 个顶点,当$ b_{ij} > 0 $时,则从顶点 i 向顶点 j 绘制 $b_{ij}$条箭头,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确定一个没有环和 2-圈的箭图 $Q$。并且,容易看出这给出了上述对应关系的逆对应。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将没有环和 2-圈的箭图与反称矩阵视为同一事物。
此时,对应于箭图的突变 $Q’ = μ_k(Q)$,反对称矩阵的突变$ B’ = μ_k(B) $也被确定,其具体的表达式如下所示:7
\[b'_{ij} = \begin{cases} -b_{ij}, & \text{若 } i = k \text{ 或 } j = k, \\ b_{ij} + [b_{ik}]_+ b_{kj} + b_{ik} [-b_{kj}]_+, & \text{若 } i, j \neq k. \end{cases} \tag{5}\]其中,符号 $[ \ ]_+$ 定义为:对于 $a$,若 $a > 0$ 则 $[a]_+ = a$;若 $a \leq 0$ 则 $[a]_+ = 0$。
3. 种子及其突变
遵循 Fomin 和 Zelevinsky的方法8,我们引入丛代数中的核心概念——种子及其突变。上一节我们引入了反称矩阵及其突变,这里我们稍作推广,考虑可反对称化的矩阵 $B$,即存在一个正定的对角矩阵$D$,使得乘积 $DB$ 是反对称矩阵9。并且对可反称化矩阵 $B$,也通过相同的公式 (5) 来定义其突变 $B’ = \mu_k(B)$。于是,可以轻易验证 $B’$ 也是一个可反称化矩阵。
接下来,为了定义丛代数,首先固定一个自然数 $n$,准备一组 $n$ 个代数独立且可交换的变量 $\mathbf{w} = (w_i)^n_{i=1}$,并考虑由 $\mathbf{w}$ 生成的 $\mathbb{Q}$ 上的有理函数域10 $\mathbb{Q}(\mathbf{w})$。然后,将任意一个可反称化矩阵 $B$ 与 $\mathbb{Q}(\mathbf{w})$ 中 $n$ 个代数独立元的组 $\mathbf{x} = (x_i)^n_{i=1}$ 构成的配对 $(B, \mathbf{x})$ 称为一个种子 (seed)。此外,对于任意 $k = 1, \ldots, n$,定义在 $k$ 处的种子突变 $(B’, \mathbf{x}’) = \mu_k(B, \mathbf{x})$ 如下:$B’$ 由 (5) 式定义的 $B’ = \mu_k(B)$ 给出;而 $\mathbf{x}’ = (x’_i)^n_{i=1}$ 则由下式给出:
\[x'_i = \begin{cases} \frac{1}{x_k} \left( \prod_{j=1}^n x_j^{[b_{jk}]_+} + \prod_{j=1}^n x_j^{[-b_{jk}]_+} \right), & i = k, \\ x_i, & i \neq k \end{cases} \tag{6}\]其中,约定求积为空时视为 $1$。此时,对于种子突变,对合性 $\mu_k^2 = \text{id}$ 也同样成立。因此,这些$x’_i$也是代数独立的,特别地,$(B’, \mathbf{x}’)$ 再次构成一个种子。
对于各种子 $(B, \mathbf{x})$,称 $B$ 为交换矩阵 (exchange matrix),称 $\mathbf{x}$ 为丛 (cluster),并称其中的各个有理式 $x_i$ 为丛变量 (cluster variable)。
此外,称关系式 (6) 为丛 $\mathbf{x}$ 的交换关系式 (exchange relation)。交换矩阵 $B$ 蕴含着从 $(B, \mathbf{x})$ 到 $(B’, \mathbf{x}’)$ 的种子变化信息,可以说扮演着类似于细胞中“DNA”的角色。并且,在种子变化时,作为 DNA 的 $B$ 自身也会发生部分改变,因此 Fomin 和 Zelevinsky 将其类比于生物学中的物种突变,并称之为“突变”。
4. 丛代数的定义
至此,定义丛代数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为了确定一个丛代数,首先任意固定一个种子 $(B^0, \mathbf{x}^0)$,称之为初始种子 (initial seed)。然后,将从初始种子 $(B^0, \mathbf{x}^0)$ 出发,通过重复所有可能的突变而得到的全部种子的集合记作 $\mathcal{S}(B^0, \mathbf{x}^0)$,并将 $\mathcal{S}(B^0, \mathbf{x}^0)$ 中所有种子 $(B, \mathbf{x})$ 包含的全部丛变量组成的集合记作 $\mathcal{X}(B^0, \mathbf{x}^0)$。通常,$\mathcal{X}(B^0, \mathbf{x}^0)$ 是一个无限集合。进而,将由 $\mathcal{X}(B^0, \mathbf{x}^0)$ 中所有丛变量生成的 $\mathbb{Q}(\mathbf{w})$ 的 $\mathbb{Z}$-子代数 $\mathcal{A}(B^0, \mathbf{x}^0)$,称为由 $(B^0, \mathbf{x}^0)$ 确定的丛代数 (cluster algebra)。此外,将属于 $\mathcal{S}(B^0, \mathbf{x}^0)$ 的种子 $(B, \mathbf{x})$ 以及属于 $\mathcal{X}(B^0, \mathbf{x}^0)$ 的丛变量,分别称为丛代数 $\mathcal{A}(B^0, \mathbf{x}^0)$ 的种子和丛变量(在应用中,也常常将丛代数的系数环 $\mathbb{Z}$ 扩展到某个域上)。
综上所述,可以说丛代数就是“一种具有满足由突变所刻画的特殊关系式的生成元的交换代数”。
此外,即使将最初准备的变量组 $\mathbf{w}$ 与初始丛 $\mathbf{x}^0$ 取为相同,也不会失去一般性(在同构意义下),因此通常可以一开始就设 $\mathbf{w} = \mathbf{x}^0$(这里也这样处理)。
让我们来看一些简单的例子。
例 1($A_1$ 型丛代数)
考虑最简单的情况 $n = 1$($n$ 称为丛代数的秩 (rank))。1 阶可反称化矩阵只有零矩阵 ($0$),它对应于仅包含一个顶点的箭图 :

注意此箭图的底图(忽略箭头方向的图)可视为 $A_1$ 型的 Dynkin 图。此时,初始种子 $(B^0, \mathbf{x}^0) = ((0), (x_1^0))$ 的突变只有一种 $(B’, \mathbf{x}’) = \mu_1(B^0, \mathbf{x}^0)$,结果为:
\[B' = (0), \quad x'_1 = 2/x_1^0\]又因为 $\mu_1^2 = \text{id}$,所以即使重复进行突变,也无法得到新的种子。因此,
\[\begin{aligned} &\mathcal{X}(B^0, \mathbf{x}^0) = \{x_1^0, 2/x_1^0\}, &\mathcal{A}(B^0, \mathbf{x}^0) = \mathbb{Z}[x_1^0, 2/x_1^0] \subset \mathbb{Q}(x_1^0), \end{aligned}\]即 $\mathcal{A}(B^0, \mathbf{x}^0)$ 的元素是初始丛变量 $x_1^0$ 在 $\mathbb{Z}$ 上的 Laurent 多项式,且其负幂次的系数为偶数。这被称为 $A_1$ 型丛代数(例如,若将系数环扩展为 $\mathbb{Q}$,则得到的就是普通的 $x_1^0$ 在 $\mathbb{Q}$ 上的 Laurent 多项式环)。
例 2($A_2$ 型丛代数)
接下来考虑 $n = 2$ 的情况,并取如下的初始交换矩阵:
\[B^0 = \begin{pmatrix} 0 & -1 \\ 1 & 0 \end{pmatrix}\]它对应于下面的箭图:

此箭图的底图是 $A_2$ 型的 Dynkin 图。将初始种子 $(B^0, \mathbf{x}^0)$ 记作 $(B(0), \mathbf{x}(0))$,并考虑如下的突变序列:
\[\cdots \overset{\mu_1}{\longleftrightarrow} (B(-1), \mathbf{x}(-1)) \overset{\mu_2}{\longleftrightarrow} (B(0), \mathbf{x}(0)) \overset{\mu_1}{\longleftrightarrow} (B(1), \mathbf{x}(1)) \overset{\mu_2}{\longleftrightarrow} (B(2), \mathbf{x}(2)) \overset{\mu_1}{\longleftrightarrow} \cdots\]那么,由 (5) 式(或由箭图的突变)可得,
\[B(t) = \begin{cases} B(0), & t: \text{偶数}, \\ -B(0), & t: \text{奇数} \end{cases}\]此外,结合 (6) 式可知,当 $t$ 为偶数时,
\[\begin{aligned} x_1(t+1) &= (x_2(t)+1)/x_1(t), \\ x_2(t+1) &= x_2(t), \end{aligned}\]而当 $t$ 为奇数时,
\[\begin{aligned} x_1(t+1) &= x_1(t), \\ x_2(t+1) &= (x_1(t)+1)/x_2(t). \end{aligned}\]然而,这正与第 1 节中考虑的演化规则 (1), (2) 完全相同。因此,根据第 1 节的结果 (3),可知上述种子突变序列具有半周期 5:
\[x_1(t+5) = x_2(t), \quad x_2(t+5) = x_1(t)\]特别地,属于 $\mathcal{S}(B^0,\mathbf{x}^0)$ 的种子是有限个(10 个),而属于 $\mathcal{X}(B^0,\mathbf{x}^0)$ 的丛变量为以下 5 个:
\[x_1^0, \quad x_2^0, \quad \frac{x_2^0 + 1}{x_1^0}, \quad \frac{x_1^0 + 1}{x_2^0}, \quad \frac{x_1^0 + x_2^0 + 1}{x_1^0 x_2^0}\]由它们生成的丛代数 $\mathcal{A}(B^0,\mathbf{x}^0)$ 称为 $A_2$ 型丛代数。
5. 丛代数的基本性质
我们概览一下在第 1 节中看到的性质,即 $A_2$ 型丛代数中的突变性质,在一般丛代数中是如何成立的。
(i) 突变的对合性
正如在种子突变的定义部分所述,这一性质总是成立。
(ii) Laurent 性
这一性质也总是成立。即,当用初始丛变量 $\mathbf{x}^0$ 的有理式表示任意丛变量 $x_i$ 时,该有理式可约简为 Laurent 多项式。实际上,Fomin 和 Zelevinsky 似乎正是以这一性质为线索,达到了种子突变的定义。
(iii) 分母向量与根的关系
对于可反称化矩阵 $B$,定义其对应的 Cartan矩阵 $C(B) = (c_{ij})_{i,j=1}^n$ 为:
\[c_{ij} = \begin{cases} 2, & i = j, \\ -|b_{ij}|, & i \neq j \end{cases}\]$C(B)$ 成为 Kac-Moody 代数中的可对称化(广义)Cartan矩阵。例如,在前一节的两个例子中,$C(B)$ 分别是:
\[(2), \quad \begin{pmatrix} 2 & -1 \\ -1 & 2 \end{pmatrix}\]它们分别对应 $A_1$ 型和 $A_2$ 型的(有限型)Cartan矩阵。一般而言,已知当 $C(B^0)$ 是有限型Cartan矩阵时,$A(B^0,\mathbf{x}^0)$ 的(除初始丛变量外的)任意丛变量关于初始丛变量的分母向量,就是与 $C(B^0)$ 对应的根系的正根,并且进一步地,分母向量与正根是一一对应的。这表明了丛代数与根系或 Lie 理论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另一方面,这也被认为是 $C(B^0)$ 为有限型时的特殊性质,在一般情况下,分母向量的行为尚未被完全了解。
(iv) 正性
“任意丛变量关于初始丛变量的 Laurent 多项式表示的分子具有正系数” 这一猜想被称为正性猜想,是丛代数基础理论中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最近,Lee 和 Schiffler 证明了在 $B^0$ 是反称矩阵的情况下该猜想是正确的,这向前迈进了一步。11
(v) 有限性
如果两个可反对称化矩阵 $B$ 和 $B’$ 可以通过有限次突变互相转换,则称 $B$ 和 $B’$ 是突变等价 (mutation equivalent) 的。$\mathcal{A}(B^0, \mathbf{x}^0)$ 的种子为有限个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存在一个可反称化矩阵 $B$,使得 $B$ 与 $B^0$ 突变等价,并且其嘉当矩阵 $C(B)$ 是有限型的。因为突变等价的可反称化矩阵所确定的丛代数(在丛代数的意义下)是同构的,所以最终得到了一个格外突出的结果:有限型丛代数的同构类的分类与众所周知的有限型根系的分类是一致的。
6. 背景及与其他领域的关联
丛代数最初是受到李理论中在各种语境下出现的代数与组合结构的启发而被引入的。Fomin 和 Zelevinsky 在其第一篇论文8中具体列举了(相互关联的)以下事项作为引入丛代数的背景:
- $SL_n$ 及其商群的坐标环的典范基,或量子群的对偶典范基。
- Grassmann 流形 $Gr_{2,n+3}$ 的 Plücker 坐标。
- 半单群的双 Bruhat 胞腔的全正基(与 Lusztig 的全正性相关)。
并且,他们提出了一个宏伟目标:将这些现象推广到与半单群相关的各种代数簇上。
此后,人们发现丛代数(或相关的代数与组合结构)超出了最初的设想,与数学的多个领域产生了关联。以下,我们不避讳内容上的重复,随机列出一些相关领域的关键词(领域的分类仅仅是为了显示丛代数影响的广泛性而做的权宜划分)。12
代数领域
- 箭图或路代数的表示论与范畴化,Auslander-Reiten 理论,2 维 Calabi-Yau 范畴。
- 预投射代数的表示论,极大幂单(unipotent)子群,Kac-Moody 群。
- 量子群的表示论,箭图簇上的偏屈层(perverse sheaves)。
- Ginzburg 分次微分代数,3 维 Calabi-Yau 范畴,稳定性条件,Donaldson-Thomas 不变量。
几何领域
- Stasheff 多胞形,Bott-Taubes 多胞形。
- Poisson 几何,Poisson-Lie 结构,Coxeter-Toda 格子。
- 2 维双曲几何:Riemann 面的三角剖分,lambda 长度13,交比(cross ratio),Ptolemy 定理,Teichmüller 理论及其高维推广,Weil-Petersson 形式。
- 3 维双曲几何:双曲体积。
- 纽结理论:辫群关系,skein 关系。
分析领域
- 二重对数函数($\operatorname{Li}_2(z)$)与量子二重对数函数。
- KP层级结构(KP Hierarchy)的孤子图。
- 精确 WKB 分析,Stokes 现象。
组合论与数学物理
- Gale-Robinson 序列,六角晶胞序列,八角晶胞序列,Somos 序列等数论与组合序列。
- 二聚体模型(dimer model)。
- 共形场论:Y-系统,T-系统,Q-系统,热力学 Bethe 假设。
- 弦理论:BPS 态计数,Hitchin 系统。
7. 系数(y 变量)简介
最后,我们想简单介绍一下在丛代数理论及应用中和丛变量同等重要的系数(y 变量),以此结束这篇简短的入门介绍。
独立于初始丛变量 $\mathbf{x}^0 = (x_i^0)_{i=1}^n$,我们新引入一组 $n$ 个可交换的变量 $\mathbf{y}^0 = (y_i^0)_{i=1}^n$。然后,与种子 $(B, \mathbf{x})$ 并行地,我们考虑一个 $n$ 阶可反称化矩阵 $B$ 和一组 $n$ 个变量 $\mathbf{y} = (y_i)^n_{i=1}$(其中 $y_i \in \mathbb{Q}(\mathbf{y}^0)$)的配对 $(B, \mathbf{y})$,并称之为 $Y$-种子(Y-seed)。对于任意 $k = 1, \ldots, n$,定义 $Y$-种子 $(B, \mathbf{y})$ 在 $k$ 处的突变 $(B’, \mathbf{y}’) = \mu_k(B, \mathbf{y})$ 如下:$B’$ 由 (5) 式确定,而 $\mathbf{y}’$ 则由下式确定:14
\[y'_i = \begin{cases} y_k^{-1}, & i = k, \\ y_i \frac{(1 + y_k)^{[-b_{ki}]_+}}{(1 + y_k^{-1})^{[b_{ki}]_+}}, & i \neq k \end{cases} \tag{7}\]$Y$-种子中的变量 $y_i$ 被称为系数(coefficient) 或 $y$ 变量(准确地说,当称为系数时,是因为 $y$ 变量也作为“系数”参与到丛变量 $x_i$ 的突变公式 (6) 中,但在此我们省略其细节)。之后,与丛变量的情况类似,从初始 $Y$-种子 $(B^0, \mathbf{y}^0)$ 出发,通过重复上述突变来考虑所得到的 $y$ 变量。
$y$ 变量最初是作为丛变量($x$ 变量)的“系数”这种辅助角色被引入的。然而,随着对 $x$ 变量与 $y$ 变量之间**对偶性 ** 认识的加深,$y$ 变量获得了与 $x$ 变量同等的地位,其重要性日益增长,在应用中有时甚至扮演主角。
最后,对于 $x$ 变量,我们定义 $\hat{y}$ 变量 $\hat{\mathbf{y}} = (\hat{y}_i)^n_{i=1}$ 如下:
\[\hat{y}_i = \prod_{j=1}^n x_j^{b_{ji}}\]那么,$\hat{y}$ 遵循与 $y$ 相同的突变规则 (7)。这表明了 $x$ 变量与 $y$ 变量之间存在某种对偶性。这个事实仅从 (5) 和 (6) 式就可以证明,因此建议大家将其作为复习内容亲自验证一下。
[DLC] 译后记
$\hat{\mathbf{y}}$的突变规则推导
这里来推导文章最后留的思考问题,首先对于$i=k$:
\[\hat{y}_k' = \prod_j {x_j'}^{b_{jk}'} = \prod_j {x_j}^{-b_{jk}'} =\hat{y}_k'\]注意这里我们用到了可反对称化矩阵的对角元是0。然后再考虑$i\neq k$:
\[\begin{aligned} \hat{y}_i' &= \prod_j {x_j'}^{b_{ji}'} = \prod_{j\neq k} {x_j}^{b_{ji}'}\cdot{x_k'}^{-b_{ki}}\\ & = \prod_{j\neq k} {x_j}^{b_{ji}'}\cdot {x_k}^{b_{ki}}\cdot \left( \prod_{l=1}^n x_l^{[b_{lk}]_+} + \prod_{l=1}^n x_l^{[-b_{lk}]_+} \right)^{-b_{ki}}\\ &=\prod_{j\neq k} {x_j}^{b_{ji}}\cdot\prod_{j\neq k} {x_j}^{[b_{ik}]_+b_{kj}+b_{ik}[-b_{kj}]_+}\cdot {x_k}^{b_{ki}}\cdot \left( \prod_{l=1}^n x_l^{[b_{lk}]_+} + \prod_{l=1}^n x_l^{[-b_{lk}]_+} \right)^{-b_{ki}}\\ &=\prod_{j} {x_j}^{b_{ji}}\cdot\prod_{j\neq k} {x_j}^{[b_{ik}]_+b_{kj}+b_{ik}[-b_{kj}]_+}\cdot \left( \prod_{l=1}^n x_l^{[b_{lk}]_+} + \prod_{l=1}^n x_l^{[-b_{lk}]_+} \right)^{-b_{ki}} \end{aligned}\]利用下面的恒等式:
\[b_{ij} = [b_{ij}]_+-[-b_{ij}]_+\]上面的式子可以最终化简为:
\[y_i'=\prod_{j} {x_j}^{b_{ji}}\cdot\prod_{j\neq k} {x_j}^{-[-b_{jk}]_+[-b_{ki}]+[b_{jk}]_+[b_{ki}]_+}\cdot \left( \prod_{l=1}^n x_l^{[b_{lk}]_+} + \prod_{l=1}^n x_l^{[-b_{lk}]_+} \right)^{-b_{ki}}\]另一方面:
\[\begin{aligned} y_i' &= y_i \frac{(1 + y_k)^{[-b_{ki}]_+}}{(1 + y_k^{-1})^{[b_{ki}]_+}}\\ &=\prod_j x_j^{b_{ji}}\cdot\left(1+\frac{\prod_m x_m^{[b_{mk}]_+}}{\prod_n x_n^{[-b_{nk}]_+}}\right)^{[-b_{ki}]_+}\cdot\left(1+\frac{\prod_m x_m^{[-b_{mk}]_+}}{\prod_n x_n^{[b_{nk}]_+}}\right)^{-[b_{ki}]_+}\\ &=\prod_{j} {x_j}^{b_{ji}}\cdot\prod_{j\neq k} {x_j}^{-[-b_{jk}]_+[-b_{ki}]+[b_{jk}]_+[b_{ki}]_+}\cdot \left( \prod_{l=1}^n x_l^{[b_{lk}]_+} + \prod_{l=1}^n x_l^{[-b_{lk}]_+} \right)^{-b_{ki}}\\ \end{aligned}\]同样这里利用了$B$对角元是0,由此可知$\hat{\mathbf{y}}$和$\mathbf{y}$遵循相同的突变规则。
关于$\mathbf{y}$被称作“系数”的原因
这里简略解释一下原文略去的「为什么$\mathbf{y}$会被称作是“系数”」这一问题。因为最早引入$\mathbf{y}$,是为每个$x_i$额外引入一个变量$y_i$,其是$\mathbf{w}$的单项式,从而把$\mathbf{x}$的在$i=k$时的突变修改为:
\[x_k^{\prime}=\frac{1}{x_k}\left(\frac{y_k}{y_k\oplus1}\prod x_i^{[b_{ik}]_+}+\frac{1}{y_k\oplus1}\prod x_i^{[-b_{ik}]_+}\right)\]$i\neq k$时依然有$x_i’ = x_i$。从这个式子就能清晰地看出“系数”的含义,其中$\oplus$的计算通过下式进行:
\[\prod_jw_j^{a_j}\oplus\prod_jw_j^{b_j}=\prod_jw_j^{\min(a_j,b_j)}\]与$1$的$\oplus$显然就是把分子上的东西直接“抹去”,另外系数本身也会突变,突变规则为:
\[\left.y_i^{\prime}=\left\{\begin{array}{ll}y_k^{-1}&\mathrm{if~}i=k,\\y_iy_k^{[b_{ki}]_+}\left(y_k\oplus1\right)^{-b_{ki}}&\mathrm{if~}i\neq k.\end{array}\right.\right.\]乍一看似乎与前面给出的$\mathbf{y}$的突变规则不同,实际上,$x$的变换规则可以重新写为下面的形式:
\[x_k^{\prime}=\frac{\hat{y}_k+1}{y_k\oplus1}x_k^{-1}\prod_ix_i^{[-b_{ik}]_+}\]这两个$\mathbf{y}$的突变规则之间是通过重定义:
\[\hat{y}_i = y_k\prod_{j=1}^n x_j^{b_{ji}}\]来联系的。然后我们来看现在新定义的$\hat{\mathbf{y}}$的突变规则,注意这个时候$\mathbf{x}$要利用带系数$\mathbf{y}$的突变规则来进行,考虑$i\neq k$:
\[\begin{aligned} \hat{y}_i^{\prime}&=y_i^{\prime}(x_k^{\prime})^{-b_{ki}}\prod_{i\neq k}x_i^{b_{ji}^{\prime}}=y_iy_k^{[b_{ki}]+}(\hat{y}_k+1)^{-b_{ki}}x_k^{b_{ki}}\prod_{j\neq k}x_j^{b_{ji}^{\prime}-[-b_{jk}]_+b_{ki}}\\ &=(y_{i}\prod_{j\neq i}x_{j}^{b_{ji}})(y_{k}\prod_{j\neq k}x_{j}^{b_{jk}})^{[b_{ki}]_{+}}(\hat{y}_{k}+1)^{-b_{ki}}=\hat{y}_{i}\hat{y}_{k}^{[b_{ki}]_{+}}(\hat{y}_{k}+1)^{-b_{ki}}\\ &=\hat{y}_i \frac{(1 + \hat{y}_k)^{[-b_{ki}]_+}}{(1 + \hat{y}_k^{-1})^{[b_{ki}]_+}} \end{aligned}\]第二行第一个等号我们利用了下面的“注意到”:
\[b_{ij}'=b_{ij}+[-b_{ik}]_+b_{kj}+b_{ik}[b_{kj}]_+=b_{ij}+[b_{ik}]_+b_{kj}+b_{ik}[-b_{kj}]_+\]不难看到这正是前面最初我们给出的$\mathbf{y}$的突变规则。$i=k$时的验证是更加平凡的。
丛代数与超对称规范理论 [山崎 雅人]
这是杂志最后一篇文章的翻译,作者是我导师,原文名「団代数と超対称ゲージ理論」
1. 丛代数与物理学家的邂逅
笔者是一名理论物理学家,但隶属于一个名为“数物連携”的研究所,与数学家的交流也很深入。理论物理学家和纯数学家无论在研究手法还是动机上都大相径庭,然而在近年来的基本粒子理论研究中,在意想不到之处邂逅纯数学中培育起来的概念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本特集所讨论的丛代数正是其中一个显著的例子。本文将阐述研究超对称场论的物理学家们是如何与丛代数相遇的。
2. 电场与磁场的和谐
我们所要考虑的是定义在我们所居住的4维时空(即3维空间加1维时间)上的规范场理论。
规范理论通过指定规范群 $G$ 来得到。考虑一个简单的例子,当规范群为 $U(1)$ 时的情况。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电磁学,$U(1)$ 规范场代表光子。在电磁学中,我们不仅考虑光子,还考虑与光子相互作用的物质场,例如电子。这是在规范群下带有某种电荷 $e$ 的场。
电磁场由磁场和电场组成,而电子只对电场带有电荷。反之,只对磁场带有电荷(将其写作磁荷 $g$)的则是磁单极子。狄拉克注意到,通过同时考虑单极子和电子,麦克斯韦方程组会变成一种关于电场和磁场互换的对称形式。更进一步,他推导出了电荷与磁荷所需满足的量子化条件:15
\[eg \in 2\pi\hbar\mathbb{Z} \tag{1}\]至此我们考虑的是只带有电荷或只带有磁荷的理论,但也可以考虑同时带有两者的粒子(Dyons)。这种情况下的量子化条件,可以用两个粒子的电荷-磁荷组合(以下简称为荷)来表示。设 $\gamma_{i=1,2} = (e_i, g_i)$,则其配对 $\langle \gamma_1, \gamma_2 \rangle$ 的量子化条件为:
\[\langle \gamma_1, \gamma_2 \rangle := e_1g_2 - e_2g_1 \in 2\pi\hbar\mathbb{Z}. \tag{2}\]可以立刻看出,这个配对是完全反对称的:$\langle \gamma_1, \gamma_2 \rangle = -\langle \gamma_2, \gamma_1 \rangle$。即使将规范群推广到更一般的可交换规范群 $U(1)^r$,除了电荷 $e$ 和磁荷 $g$ 分别变为具有 $r$ 个分量的向量 $\vec{e}, \vec{g}$ 之外,量子化条件是一样的。(2) 式引入的荷的配对,正如后文将看到的,对于箭图的定义非常重要。
3. 四维 $\mathcal{N}=2$ 理论的库仑分支
到目前为止的讨论,并未直接需要例如规范场拉格朗日量的具体形式。因此,即使最初是从非阿贝尔规范群的设定出发,只要最终规范群破缺到其可交换部分,就可以预期讨论是类似的。
提到规范群破缺,首先想到的是希格斯机制:例如,属于 $SU(3)$ 规范群基本表示的夸克场如果获得期望值,规范群就会发生破缺。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规范群通常会被完全破缺,甚至连可交换规范群也不会留下。
于是,我们假设存在一个场 $\sigma$,它在规范群变换下按伴随表示变换(即在规范群元 $g$ 下按 $\sigma \to g^{-1}\sigma g$ 变换),并且该场获得了(一般的)期望值。此时,规范群的非交换部分会被破缺,但规范群的可交换子群$U(1)^r$ 会全部保留下来(伴随表示在可交换子群的变换下不变)。这里的 $r$ 是一个被称为规范群的秩的量。
在这种情形中,我们考虑一个典型例子:四维 $\mathcal{N}=2$ 理论。超对称性是一种将玻色子与费米子互换的对称性,在 $\mathcal{N}=2$ 超对称性下,存在两个独立的超对称变换,将这两个变换组合起来,可以使玻色子转变为另一个玻色子。特别地,对于作为玻色子的规范场 $A_\mu$,存在另一个玻色子与之配对,那就是先前提到的标量场 $\sigma$。规范场按规范群的伴随表示变换,因此与之配对的 $\sigma$ 也如预期的那样按伴随表示变换。在具有 $\mathcal{N}=2$ 超对称性的理论中,存在 $\sigma$ 获得期望值的真空,在此真空下,可交换规范场得以保留,被称为库仑分支16。我们将考察在此真空中,四维 $\mathcal{N}=2$ 理论在低能下的行为。求解这种低能有效理论的,是90年代中期出现的Seiberg-Witten 理论,本刊此前也曾多次介绍。丛代数正是在讨论这一经典框架及其推广的过程中出现的。
4. 从 BPS 粒子到箭图
在库伦分支上,规范群虽是阿贝尔的,但我们的出发点是非阿贝尔规范群的规范理论。当物质场的数量并不太多时,理论具有渐近自由性,在我们感兴趣的低能区处于强耦合区域,直接解析并不容易。
在此,我们不直接研究理论本身,而是转而研究理论的谱。也就是说,我们将考虑存在带有何种电荷的稳定粒子,以及它们的数量。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 $\mathcal{N} = 2$ 超对称性所带来的限制,我们将特别考虑仅保留最大超对称性(在当前情况下是一半)的粒子。我们称此类粒子为 BPS粒子(在当前情况下,确切地说是 $\frac{1}{2}$ BPS 粒子)。
BPS 粒子的一个特征是,带有电荷 $\gamma$ 的 BPS 粒子的质量由该电荷所确定的复数 $Z_\gamma$(中心荷)的绝对值 $|Z_\gamma|$ 决定。另一方面,$Z_\gamma$ 的相位部分指定了它保留了 $\mathcal{N} = 2$ 超对称性中的哪一个 $\mathcal{N} = 1$ 子代数。此外,$Z_\gamma$ 对 $\gamma$ 是线性的:$Z_{\gamma_1 + \gamma_2} = Z_{\gamma_1} + Z_{\gamma_2}$,$Z_{n\gamma} = nZ_\gamma$。
在库伦分支上,存在未被破缺的阿贝尔规范群 $U(1)^r$,因此粒子带有该规范群的电荷 $\gamma \in \Gamma$。这里 $\Gamma$ 是所有允许电荷的集合,它满足具有完全反对称配对的量子化条件(式 (2))。
因为我们是从相对论性局域场论出发的,CPT 定理成立。特别地,如果存在带有电荷 $\gamma$ 的粒子,则必然也存在带有相反电荷 $-\gamma$ 的反粒子。因此,在计数粒子时,我们只需考虑两者中的某一个即可,$\Gamma$ 可分解为两个不相交的并集:
\[\Gamma = \Gamma_{\text{正}} \cup \Gamma_{\text{负}}\]然而,这种分解并非唯一。为了我们的目的,可以通过固定某个辐角 $\zeta$,并收集前面引入的复数 $Z_\gamma$ 在复平面上辐角位于 $[\zeta, \zeta + \pi]$ 区间内的那些电荷,来定义 $\Gamma_{\text{正}}$(图 1):
\[\gamma \in \Gamma_{\text{正}} \longleftrightarrow \text{Im}(e^{-i\zeta} Z(\gamma)) > 0 \tag{4}\]
现在,我们来由此定义箭图 。设生成 $\Gamma_{\text{正}}$ 的一组基为 ${\gamma_i}$ 17。
\[\Gamma_{\text{正}} = \bigoplus_i \mathbb{Z}_{\geq 0}\gamma_i \tag{5}\]此时,我们通过下式定义一个半对称矩阵 $B = (b_{i,j})$,从而定义箭图(参见本特集中西知樹的文章18):
\[b_{ij} :=\left \langle \gamma_i, \gamma_j\right\rangle \tag{6}\]我们称此箭图为 BPS 箭图。如前所述,由于配对是反对称的,请注意 $b_{ij}$ 给出的也是反对称矩阵。
式 (6) 的定义看似凭空而来,但其背后确有很好的物理意义。BPS 粒子是存在于四维 $\mathcal{N} = 2$ 超对称规范理论中的粒子,其本身保留了一半的超对称性。因此,站在该粒子上观察者的立场来看,就好像出现了具有四维 $\mathcal{N} = 1$ 超对称性的量子力学(粒子所对应的场论即量子力学)。先前定义的箭图给出了此超对称量子力学(箭图超对称量子力学)定义所需资料。
具体而言,可以如下操作:箭图的顶点对应于在电荷上定义的一组基中的一个元素 $\gamma_i$。当考虑电荷 $\gamma = \sum_i n_i \gamma_i$ 时,对于第 $i$ 个顶点,我们考虑规范群 $U(n_i)$;对于从顶点 $i$ 出发连接到顶点 $j$ 的边,我们对应一个在 $U(n_i) \times U(n_j)$ 下按 $(n_i, \bar{n}_j)$ 表示变换的场 1920。
5. 箭图的突变
至此,我们已对箭图及其物理意义进行了说明,但目前的阐述仍存在不足之处。即正负电荷的划分并非唯一。这一点从(4)式依赖于辐角$\zeta$便可明确看出。具体而言,当$\zeta$越过某个基底元素$\gamma_k$的辐角时,$\Gamma_{\text{正}}$便会发生变化,继而导致箭图发生改变(图2)。

假设原本带正电荷的$\gamma_k$变为带负电荷。此时显然必须将$-\gamma_k$纳入新的基底中:
\[\gamma'_k = - \gamma_k\]但为保持(5)式成立,则需同时更换其他基底元。其结果已知为:
\[\gamma_i \rightarrow \gamma_i + [b_{ik}]_+ \gamma_k\]这里 $[x]_+ := \max(x,0)$。此时根据(6)式的定义,箭图将发生如下变化:
\[\begin{aligned} &b_{ik} \rightarrow -b_{ik}, \\ &b_{ij} \rightarrow b_{ij} + [b_{ik}]_+ b_{kj} + [b_{jk}]_+ b_{ik} \end{aligned} \tag{9}\]这正对应中西知樹的文章中(5)式所引入的箭图突变 $B \rightarrow B’ = \mu_k(B)$ 。如此,我们便抵达了突变的源头。
此处不对(8)式进行证明,从箭图表示论角度展开的论述可参阅文献21第3.1.2节。此外,作为更直接的说明,存在一种基于先前所述超对称量子力学的对偶性的解释。基于相同的箭图,亦可定义二维超对称场论,而箭图的突变恰恰体现了这种对偶性22。这种突变维数约化至一维量子力学后,即构成本文所述的箭图的突变。
6. 丛变量$y$与圈算符
在丛代数中,丛变量$x$和丛变量$y$(系数)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事实上,在我们的设定中,丛变量$y$是作为库伦分支的坐标而出现的。
这里我们不考虑一般的四维 $\mathcal{N} = 2$ 理论,而是考虑将 $A_{N-1}$ 型六维 (2,0) 理论紧致化到带标记点(即,有洞的)黎曼面 $C$ 上所得的理论:
\[\text{六维理论:}\mathbb{R}^4 \times C \longrightarrow \text{四维理论:}\mathbb{R}^4 \tag{10}\]此处,六维 $A_{N-1}$ 型 (2,0) 理论是本质不明的谜之理论,直接使用并无助益,但我们很清楚其 $S^1$ 紧致化会给出五维 $\mathcal{N} = 2$ $SU(N)$ 规范理论。因此,考虑将 $\mathbb{R}^4$ 中的一个方向紧致化到 $S^1$ 上,则有:
\[\text{六维 }A_N\text{ 型理论:}\mathbb{R}^3 \times S^1 \times C \longrightarrow \text{五维 } SU(N) \text{ 规范理论:}\mathbb{R}^3 \times C\tag{11}\]这是可以具体实现的。(11) 中是先进行 $S^1$ 紧致化,但如果改变顺序先对 $C$ 进行紧致化,则 (10) 中的四维理论将被 $S^1$ 紧致化为三维理论:
\[\text{四维理论:}\mathbb{R}^3 \times S^1 \longrightarrow \text{三维理论:}\mathbb{R}^3\tag{12}\]现在,使用五维理论的拉格朗日量分析 $C$ 上的 BPS 方程时,会出现称为Hitchin moduli的模空间23。该空间根据复结构的取法有几种描述,其中之一是 $PSL(N,C)$ 平坦联络的空间。即, $C$ 上满足
\[F = d\mathcal{A} +\mathcal{ A} \wedge \mathcal{A} = 0 \tag{13}\]的复联络 $\mathcal{A}$ 的全体,再模去规范变换2425。这样表示的 $PSL(N, C)$ 平坦联络空间,已知存在自然的坐标(Fock-(Goncharov) 坐标26)。
此处为简单起见,我们考虑 $N = 2$ 的情况。考虑以 $C$ 的洞为顶点的三角剖分(此类三角剖分称为理想三角剖分),通过在各个三角形上画图3所示的箭图,可以得到画在 $C$ 上的箭图 $B = (b_{ij})$(这里,假设 $C$ 具有足够数量的洞,且存在这样的三角剖分)。

此时,将箭图的顶点27 $i$(理想三角剖分的边)与复变量 $y_{\gamma_i}$ 对应起来,则该变量成为Hichin模空间的坐标,并且数学上已知其上的辛形式由下面简单的形式
\[\{y_{\gamma_i}, y_{\gamma_j}\} = b_{i,j} \tag{14}\]给出。另外,令 $y_{\gamma_1 + \gamma_2} := y_{\gamma_1} + y_{\gamma_2}$ ($y_{n\gamma} = n y_\gamma$),对一般的 $\gamma \in \Gamma$ 定义 $y_\gamma$ 会比较方便。
若将(14)式视为经典力学中熟知的泊松括号,则 $y_{\gamma_i}$ 无非是有限维经典力学相空间的坐标。与(2)式比较可知,顶点27 $i$ 对应于正电荷的基 $\gamma_i$,而从图3确定的箭图自然可等同于四维 $\mathcal{N}= 2$ 理论的BPS箭图。
进而,坐标 $y_\gamma$ 被认同为由电荷 $\gamma$ 指定的红外理论中的圈算符的期望值28。此处圈算符指一维延展的算符,其代表例子是Wilson线,即规范场沿回路的积分:四维理论中的圈算符,当在 $S^1$ 上对四维理论进行维度约化(12)时,若其缠绕 $S^1$ 方向,则会成为三维理论中的粒子。四维中的库伦分支是由以伴随表示取值的场 $\sigma$ 的期望值参数化的。维度约化到三维时,规范场在 $S^1$ 方向上的积分会给出三维中新的实标量场 $\bar\sigma$。$\sigma$, $\bar\sigma$ 成对地参数化三维的库伦分支。因此,可以理解为将圈算符的期望值复化,自然会给出库仑分支指定的坐标。
不严格考虑三维,而保持 $S^1$ 的半径 $R$ 为有限时,会发生什么?回到(11),这是从五维理论向六维理论的提升。用超弦理论的语言来说,这是IIA型超弦理论的五维膜(D4膜)提升为M理论的六维膜(M5膜)的过程。
此时,三维中的粒子提升为四维的圈算符。与粒子不同,已知一般带有电荷-磁荷的圈算符会成为互不对易的算符29,因此坐标 $y_{\gamma_i}$ 应该被替换为不对易的算符 $\hat{y}_{\gamma_i}$。自然的量子化是通过将有限维相空间(14)的泊松括号替换为算符的对易关系而得:
\[[\hat{y}_{\gamma_i}, \hat{y}_{\gamma_j}] = i\hbar b_{i,j}\tag{15}\]或者,若使用由 $\hat{Y}_\gamma = e^{\hat{y}_\gamma}$ 定义的变量,则得到所谓的量子环面:30
\[\hat{Y}_{\gamma_1} \hat{Y}_{\gamma_2} = q^{\left\langle \gamma_1, \gamma_2 \right\rangle} \hat{Y}_{\gamma_2} \hat{Y}_{\gamma_1}\tag{16}\]其中,$q := e^{i\hbar}$,经典极限是 $q \to 1$。由此可见,向四维理论(即M理论)的提升,其实是对Hichin模空间进行量子化31。
7. 箭图突变与翻转
至此,我们通过考察 M 理论看到了Hichin模空间被量子化,那么箭图的突变又是如何被量子化的呢?
在此,我们先对这个突变进行组合上的说明。既然箭图是由理想三角剖分确定的,那么箭图的模糊性就源于理想三角剖分的模糊性32。
众所周知,理想三角剖分的任意性,可通过重复进行交换理想四边形对角线的操作(称为翻转)来穷尽。因此,我们需要研究在翻转操作下变量 $\hat{Y}_\gamma$ 如何变化。

首先,在边 $k$ 上进行翻转时,对应的箭图 $B$ 会转变为顶点$k$处的突变 $\mu_k(B)$(图4)。此时,电荷根据(7)式和(8)式发生变化,因此对应的变量 $\hat{Y}_{\gamma_k}$ 也自然地按下式变化:
\[\mu_k : \begin{cases} \hat{Y}_{\gamma_k} \rightarrow \hat{Y}_{-\gamma_k} = \hat{Y}^{-1}_{\gamma_k}, \\ \hat{Y}_{\gamma_i} \rightarrow \hat{Y}_{\gamma_i + [b_{ik}]_+ \gamma_k} & (i \neq k) \end{cases} \tag{17}\]实际上可以确认,当 $\hat{Y}_{\gamma_i}$ 满足 (14) 式时,这样变换后的 $\hat{Y}_{\gamma}$ 满足对新箭图 $B’ = \mu_k(B)$ 的 (14) 式,证明需使用下式:
\[\hat{Y}_{\gamma_i + [b_{ik}]_+ \gamma_k} = q^{-\frac{1}{2}[b_{ik}]_+ b_{ki}} \hat{Y}^{[b_{ik}]_+} \hat{Y}_{\gamma_i} \tag{18}\]然而事情并未结束。实际上,还需进一步进行如下变换:
\[K_{\gamma_k} : \hat{Y}_{\gamma_i} \rightarrow \Psi_q(\hat{Y}_{\gamma_k})^{-1} \hat{Y}_{\gamma_i} \Psi_q(\hat{Y}_{\gamma_k}) \tag{19}\]其复合
\[\bar{\mu}_k := K_{\gamma_k} \mu_k \tag{20}\]才是由翻转操作所诱导的变换。这里,$\Psi_q(x)$ 是称为量子双对数函数的特殊函数33,由以下递推关系定义:
\[\begin{aligned} &\Psi_q(qx;q) = (1 + q^{1/2}x)^{-1} \Psi_q(x;q),\\ &\Psi_q(0;q) = 1 \end{aligned}\tag{21}\]更具体地写,记 $\hat{Y}_i := \hat{Y}_{\gamma_i}$,则 $\bar{\mu}_k$ 的作用由下式给出:
\[\hat{Y}_k \rightarrow \hat{Y}^{-1}_k \tag{22}\]以及对于 $i \neq k$ 的情况,记 $s_{jk} := \text{sgn}(b_{jk})$,则有:
\[\hat{Y}_j \rightarrow \prod_{n=0}^{|b_{jk}|-1} \left(1 + q^{-(n+\frac{1}{2})s_{jk}} \hat{Y}^{-s_{jk}}_{k}\right)^{-s_{jk}} \hat{Y}_j \tag{23}\]这正是量子丛代数中量子 $y$ 变量的变换法则。
特别地,若令 $q = 1$,则得到如下变换法则:
\[\begin{aligned} &Y_k \to Y_k^{-1},\\ &Y_j \to \left(1 + Y_k^{-\text{sgn}(b_{jk})}\right)^{-b_{jk}}Y_j. \end{aligned}\tag{24}\]这正是在其他一些文章中也已出现过的(经典)丛代数的系数($y $变量)的变换法则。
以上我们只考虑了单次箭图突变,但也可以进行多次突变。其结果是箭图 $B$ 变化为另一个箭图 $B’$:34
\[B' = \bar\mu_k \cdots \bar\mu_1(B) \tag{25}\]而算符 $\bar \mu_k$ 的积给出了从 $B$ 的量子环面到 $B’$ 的量子环面的映射:
\[\bar\mu_k \cdots \bar\mu_1 \tag{26}\]这种形式的算符被用于描述 Kontsevich 和 Soibelman 的壁跨越现象(wall-crossing)中的公式,并相关地用于量子双对数函数的恒等式和 $Y$ 系统的构造。此外,它也可以解释为出现在四维 $\mathcal{N} = 2$ 理论边界上的三维 $\mathcal{N} = 2$ 理论的配分函数35。后者与三维流形的几何也有关联,其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理论(参见本特集中寺嶋氏的文章以及文献 36)。
8. 簇代数的彼岸
以上,我们阐述了丛代数的结构在超对称规范理论的一个特定语境中是如何出现的。丛代数,无非是描述了四维 $\mathcal{N} = 2$ 理论中圈算符所构成的代数,以及该代数在电荷格(charge lattice) $\Gamma_{\text{正}}$ 的更换下如何变化。可以预期,对于更一般的超对称规范理论,通过考虑圈算符所构成的代数,也能得到类似的结构(例如参见Journal of Physics A 推出的数学物理中的丛代数特刊)。
有趣的是,纯粹出于数学兴趣而产生的丛代数,在超对称场论的物理的考察中也是一个重要的结构。笔者本人起初也对丛代数抱有敬而远之的态度,但时常会零星地听到关于它的信息。之后,在自己的研究中意识到了它的强大之处,便转而接受并沿用至今37。希望通过这篇文章,能让各位读者对丛代数产生些许亲近感。
正如本特集所明确展示的那样,簇代数出现在多种多样的语境中。可以说,其在超对称场论中的现身,仅仅是簇代数众多面貌中的一种38。然而,我们至此所讨论的超对称规范理论的物理,其内涵远比作为骨架的代数性的簇代数结构本身更为丰富。丛代数的多钟侧面得以汇聚呈现的同时,也持续激发着数学的新发展。每当思索还能从群代数中汲取何种智慧、前方又潜藏着怎样的未知时,笔者便会心潮澎湃。
[DLC]译后记
文中涉及到一个关键构造是理想三角分割及其翻转与箭图的联系,其详细论述可以在math/0608367中找到,本期杂志中寺嶋的文章进行了简要的论述,这里做一些摘录总结。
其实我只需要给一个例子你大概就懂流形的三角剖分和箭图是怎么联系起来的了,就是以那些洞为0-胞腔去构造2-胞腔,比如对于含有五个洞的球面,其三角剖分显然可以取做:

前面的图3已经告诉你怎么把一个子三角形转换成对应的箭图,这其实有点类似去做对偶剖分。那么把这个三角剖分转换为箭图只需要把每个剖分后得到的三角形都那样转换为对应的箭图就好了,最终得到的结果如下:

但是显然又不止一个这样的三角剖分,注意到图上除了有三角形(我们这里的三角形指的都是曲面上的曲边三角形),还会因为两个三角形共用一条边构成一个带有对角线的四边形,但是一个四边形剖分成三角形的时候显然有两条对角线供我们用,所以对于一个四边形我们会有两种三角剖分的手段,也就是图4说的事情。黎曼面上任何两个不同的三角剖分都可以通过把那些四边形的对角线“翻转”以下互相得到。而这恰恰对应箭图关于对角线上的那个顶点(或者说四边形的重心)之间的突变。这一点可以用第二篇文章给出的箭图突变的图像化定义看出。
个人的一些评述
这一节并不是文章翻译,而是本人根据个人散射振幅领域背景,对从代数方法的一些基于散射振幅应用的评述。
我第一次了解到丛代数是关注到一些振幅多面体相关的工作,不过后面也没有深入研究,这里想就我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做说明,大概是有关$\mathcal{N}=4$ SYM理论费曼积分中发现的一些丛代数结构。39
多对数积分及其符号
相对比较独立的一节,以最少的代价对下文需要使用的概念做一些阐述。
费曼积分里面涉及到传播子之类的函数积分,我们都知道$\frac 1x$积分一次之后是个对数,而往往不只有一个传播子要积分,所以就会出现对数的积分,由此递归定义多对数函数如下:
\[G(a_1,\ldots,a_n;z):=\int_0^zd\log(t-a_1)G(a_2,\ldots,a_n;t),\quad G(;z):=1\]此外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的直接定义:
\[G(\underbrace{0,\ldots,}_k0;z):=\frac{1}{k!}(\log z)^k\]多对数函数一个比较常用的概念是“符号”,多对数函数的有理线性组合其实是一个$\mathbb{Q}$系数分次代数,根据$a$的个数(也叫权)自然分次,而且是一个Hopf代数。为什么是代数可以根据下面的乘法恒等式看出:
\[G(a_1,...,a_m;z)G(b_1,...,b_n;z)=\sum_{c\in \mathrm{shuffle}(a;b)}G(c_1,...,c_{m+n};z)\]这里shuffle表示洗牌序,不熟悉的读者可以见本网站关于BCJ相关内容的讨论,或者见任何一本散射振幅的教材。对于如下的嵌套积分:
\[T_k=\int_a^bd\log R_1\circ\cdots\circ d\log R_k\]定义其符号为:
\[\mathcal{S}(T_k):= R_1\otimes\cdots\otimes R_k\]注意到对于多对数函数:
\[dG(a_1,...,a_n;z)=\sum_{i=1}^nG(a_1,...,\hat{a}_i,...,a_n;z)d\log\frac{a_i-a_{i-1}}{a_i-a_{i+1}},\quad a_0:= z,a_{n+1}:=0\]从而可以递归定义其符号:
\[S(G(a_1,...,a_n;z))=\sum_{i=1}^nS(G(a_1,...,\hat{a}_i,...,a_n;z))\otimes\frac{a_i-a_{i-1}}{a_i-a_{i+1}}\]然后线性扩展定义在整个多对数函数构成的Hopf代数上。最终得到的符号是$a\otimes b\otimes c\cdots$的形式,其中的每个因子$a,b,c,\ldots$我们称作是这个符号的字母,所有字母的集合就叫做这个超越函数的字母表。
符号也构成一个分次代数,可以进行加法和乘法,由于定义的时候是用$d\log$自变量定义的,所以加法其实类似$\log$加法,最终等价于对自变量乘法。而符号的乘法则根据多对数函数之间的乘法读出来。另外,在定义符号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要模去常数的,因为$d\log(cx)=d\log x+d\log c$,显然第二项是$0$,所以我们有下面的三个关系式:
\[\begin{aligned} R_1\cdots\otimes(R_aR_b)\otimes\cdots R_k=&R_1\cdots\otimes R_a\otimes\cdots R_k\\&+R_1\cdots\otimes R_b\otimes\cdots R_k,\\R_1\cdots\otimes(cR_a)\otimes\cdots R_k=&R_1\cdots\otimes R_a\otimes\cdots R_k\\ (a_1\otimes\cdots\otimes a_m)\cdot(b_1\otimes\cdots\otimes b_n)=&\sum_{c\in \mathrm{shuffle}(a;b)}c_1\otimes\cdots\otimes c_{m+n} \end{aligned}\]自然地,如果其中有个常数因子在符号里头,那么整个符号就直接是0。显然把超越函数会丢失掉一些信息,但是有些时候如果我们能事先知道某个超越函数的字母表,有希望还原出这个特殊函数。比如考虑:
\[F(x)=\mathrm{Li}_2(x)+\mathrm{Li}_2(1-x)+\log(x)\log(1-x)\Rightarrow \mathcal{S}(F(x))=0\]而权为2且符号为0的超对数函数由$\log(-1)\log(x)=-i\pi\log(x)$和$\mathrm{Li}_2(1)=\pi^2/6$张成。所以这个有理线性多对数函数的组合实际上是$-i\pi\log(x)$和$\pi^2/6$的有理系数组合。然后再结合解析性,在$x\in(0,1)$内$F(x)\in\mathbb{R}$,而且$\lim_{x\to 0^+}F(x)=\mathrm{Li}_2(1)$,所以只能有:40
\[F(x)=\mathrm{Li}_2(x)+\mathrm{Li}_2(1-x)+\log(x)\log(1-x)=\frac{\pi^2}{6}\]这种方法是否能推广,其关键在于对于一个字母表,我们能得到其张成的最一般的符号:
\[\sum_Ic_Ia_1^I\otimes\cdots\otimes a_n^I\]而何时这个符号会是一个多对数函数的符号?需要如下的可积性条件对任意的$i$成立:
\[\sum_Ic_Ia_1^I\otimes\cdots\otimes a_{i-1}^I\otimes\hat{a_i^I}\otimes\widehat{a_{i+1}^I}\otimes\cdots\otimes a_n^Id\log a_i^I\wedge d\log a_{i+1}^I=0\]费曼积分中的丛代数结构
上面我们了解了多对数函数,也知道了可以从中提取出字母表这种线性的、运算相对简单的信息,虽然提取过程中会导致失真。那么我们自然会问,费曼积分有非常明显的多对数函数的形式,他的字母表有什么样的性质呢?或许对于$\mathcal{N}=4$ SYM,丛代数能给出这个答案。

考虑上图的盒子形费曼图,这里的$x_i$是和$p_i$对偶的一套坐标,在SYM振幅里面经常被使用,因为是在对偶胞腔里面定义的,所以自然会满足动量守恒。有趣的是,任意圈的表达式都可以被精确计算:
\[\mathcal{I}^{(L)} := \frac{f^{(L)}}{z-\bar z},\quad f^{(L)}=\sum_{m=L}^{2L}\frac{m!\left(-\log(z\bar{z})\right)^{2L-m}}{L!\left(m-L\right)!\left(2L-m\right)!}\left(\mathrm{Li}_m(z)-\mathrm{Li}_m(\bar{z})\right)\]这里引入了交比:
\[\frac{z\bar{z}}{(1-z)(1-\bar{z})}=\frac{x_{13}^2x_{57}^2}{x_{15}^2x_{37}^2},\quad\frac{1}{(1-z)(1-\bar{z})}=\frac{x_{17}^2x_{35}^2}{x_{15}^2x_{37}^2}\]从任意圈的表达式可以明显看出,无论多少圈,对应的字母表都是一样的,都是
\[\{z,\bar{z},1-z,1-\bar{z}\}\]而这正是两套$A_1$丛代数的$x$丛变量,也等价于$D_2$丛代数的$x$丛变量。
这个例子相对而言是比较平凡的,我们自然会问是否对更一般的费曼图,也是任意圈的字母表都会对应到某个丛代数?要完全验证这一点是相当困难的,不过人们已经发现了不少例子,比如下面的五边形阶梯:

任意圈的字母表如下:
\[\{u,v,w,1-u,1-v,1-w,1-uw,1-vw,1-u-v+uvw\}\]取变换:
\[u=\frac{1}{1+z_2},\quad v=\frac{1}{1+z_3},\quad w=1+z_1\]得到丛代数文献中惯用的$D_3\cong A_3$丛代数的丛变量:
\[\{z_1,z_2,z_3,1+z_1,1+z_2,1+z_3,z_1-z_2,z_1-z_3,z_1+z_2z_3\}\]再比如对于有两个五边形的情况:

虽然和前面所有的这种盒子阶梯积分一样,我们都能写下其递推方程,但是随着五边形的加入,外腿数目增多,递推方程的分析愈发困难。对于这个情形文献41计算到了四圈情况,并证明了其字母表正是$D_4$丛代数的丛变量。
评述
其实在$\mathcal{N}=4$ SYM振幅中发现丛代数结构本身某种程度上并不令人意外,因为$\mathcal{N}=4$ SYM振幅本身就具有Grassmannian结构,而前面说过丛代数最初提出就是在Grassmannian的Plücker坐标中提出的,从这一点上看是十分自然的。但是上面我们只举了三个例子,原因是到了更高点之后我们发现从Grassmannian去解释对应的丛代数应该是无限型的丛代数,而费曼积分的字母表显然是有限的,所以问题就在于如何丛无限的丛代数中提取出有限个字母表。目前有一些结果,但是离真正推广还有很大的距离。所以目前来说只在一些特殊的例子中发现了丛代数结构,对于一般的情况还有待研究。
或许有人会觉得这有可能只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费曼积分本来就和多对数函数有很大关联,同时对于特殊的$\mathcal{N}=4$ SYM理论本身又和Grassmannian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丛代数结构应该在更广的范围内也存在。
还有一点我不太满意就是我只看到了他们argue费曼积分出来的字母表刚好是cluster代数的生成元,而且能从Grassmannian上看出一些解释,但是cluster代数最重要的突变操作是如何联系费曼积分的我并没有看到相关说明,或许是因为我目前看的还比较少。
原文脚注及译注
-
Involution,意思是操作两次之后相当于没操作 ↩
-
这个日语汉字对应中文“团” ↩
-
cluster的假名拼法 ↩
-
「環境ナノクラスター」、「食クラスター」、「医療クラスター」 ↩
-
日语是ベキ ↩
-
math/0305434, math.QA/0404446, math/0104151, math/0208229,hep-th/0111053, math/0602259 ↩
-
第二个突变规则也可以简化为:$b_{ij}=b_{ij}+\operatorname{sgn}(b_{ik})[b_{ik}b_{kj}]_{+}$ ↩
-
原文这句话表述有些问题且模糊,反正我是没看懂,我进行了稍微改写,另外从这个“可反对称化”的定义可以看出仍有$B$的对角元是$0$,这一点在后面的计算中有用到。 ↩
-
在日语中「域」对应的是「体」,注意不要和中文里面的“体”这类数学对象搞混了 ↩
-
一般情况仍然尚不明确,这个特殊情况的证明在论文1306.2415中可以找到 ↩
-
对一些中文译名尚不明确的数学术语标注了英文 ↩
-
见1210.5569 ↩
-
原文这个公式有误,翻译时已做更正 ↩
-
关于这些内容,请参阅例如本刊2014年7月号的特集《磁单极子之谜》 ↩
-
之所以被称为“分支”(枝),或许可以想象是因为从特定点(例如具有共形不变性的点)延伸出了多个“分支”。 ↩
-
这种基是否存在并不显然。例如,$\mathcal{N}=4$ 理论不具有这样的有限基。 ↩
-
也即本文选译的上一篇文章。 ↩
-
准确地说,还需要通过超势来指定相互作用。 ↩
-
超对称量子力学的真空模空间,在数学上等同于带有势的箭图的稳定表示所构成的模空间,与木村氏的文章(也是该期刊的文献,不过本文没有选译)中出现的箭图簇有密切关系。 ↩
-
指的是:1112.3984。 ↩
-
指的是:1406.2699。 ↩
-
Hitchin系统是超凯勒流形,具有由 $\mathbb{P}^1$ 参数化的复结构。 ↩
-
准确地说,此外还存在与 $\mathcal{A}$ 对易的标量场,它们描述了库伦分支以外的真空分支(参见1404.7521)。 ↩
-
不过,在 $C$ 的洞处会施加指定 $\mathcal{A}$ 的和乐的边界条件。 ↩
-
参考文章:math/0311149。 ↩
-
参考文章1006.0146和0907.3987。 ↩
-
参考文章:A. M. Polyakov, Mod. Phys. Lett. A 3, 325 (1988) ↩
-
译者认为叫这个名字或许是因为注意到环面基本群:$\pi_1(T^2)=\langle a,b\mid aba^{-1}b^{-1}=1\rangle$ ↩
-
不过,此主张最终应由场论的直接计算来证实。关于此方向请参阅例如文献1111.4221。 ↩
-
这里我们是凭空组合地给出了三角剖分,但实际上有更物理的解释:BPS状态由黎曼面 $C$ 上的测地线给出,通过考虑该测地线族,可以构成理想三角剖分。此外,该三角剖分依赖于 $\zeta$ 的值,改变它会引起三角剖分的变化(见1006.0146和0907.3987)。(在更严格的设定下)其构造在本特集中的岩木氏的文章(也是该期刊的文献,不过本文没有选译)中有所论述。 ↩
-
参考文献:hep-th/9310070。 ↩
-
原文下面这个式子是$\mu$而不是$\bar\mu$,我觉得应该是后者 ↩
-
参考文献:1301.5902 ↩
-
参考文献是山崎雅人为数理科学2012 年 10 月号 写的文章「場の理論の分解学」以及山崎雅人所著书籍『場の理論の幾何』。遗憾的是这两篇文章目前都只有日语版本。 ↩
-
就笔者而言,通常在经历种种曲折之后所学到的知识往往更有用处。 ↩
-
欲窥探丛代数在数理物理中的广泛应用,可参考例如文章中提到的Journal of Physics A的丛代数特刊。 ↩
-
如果你感兴趣我推荐你读一下理论所李振杰学长的博士论文以及2103.02796。 ↩
-
He, S., Li, Z. & Yang, Q. Notes on cluster algebras and some all-loop Feynman integrals. J. High Energ. Phys. 2021, 119 (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