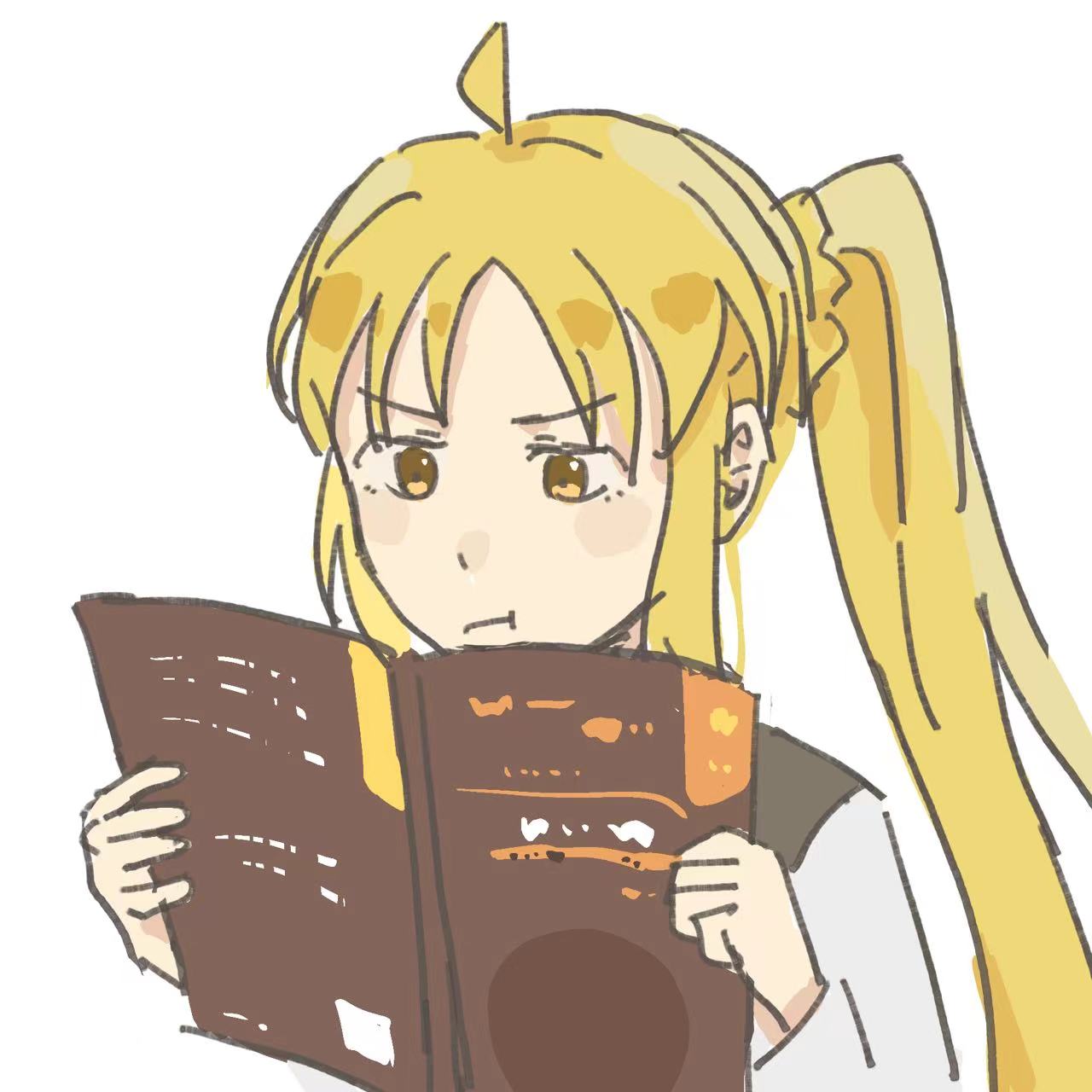七月主要是在家学习,无聊的一些对自己贫瘠的物理数学知识的吐槽罢了。
七月在家学习
2025-07-01
今天看完Hawking奇性定理的证明,对大爆炸宇宙学理解更深刻了一些。Hawking奇性定理是在说整体双曲(有柯西面)时空,在假定强能量条件的情况下,一定是测底不完备的,更强一点说就是从柯西面往过去演化足够长事件后所有测地线都不能再延拓。当然,这让我们很直观的想象是这些测地线碰到了奇点,也就是大爆炸的奇点,不过Hawking的原始表述还无法达到这一推断。
首先是在学宇宙学的第一节课肯定会讲到在各项均匀的大尺度结构假设下,在共动参考系下写下FRLW度规,而这个共动参考系是大多数人第一感觉很迷糊的地方,今天来看其实无非就是雷乔杜里参考系,就是用柯西面上的坐标$x$以及到柯西面上点的测地线固有时$\tau$来标记,这样无论怎么演化,在这个坐标系下所有点都是随着参考系一起动的,他们的$x$坐标都是不变的,所以我们说真正测到的距离应该要乘上一个膨胀因子$a(t)$。
其次就是暴涨是发生在大爆炸之前,奇点是非常丑陋的,而暴涨就避免了这一点,告诉我们在大爆炸之前还有一个暴涨升温的阶段。暴涨模型比如慢滚模型,暗物质这些,用来破坏Hawking奇点定理其实都是在强能量条件这件事上做文章。因为强能量条件就是辐射压和正常物质产生的能动张量,如果采用正宇宙学常数或正标量势能就能顺利违背强能量条件从而否定Hawking论断,从而避免奇点的出现。
2025-07-02
今日又是被Witten的论文说服的一天,具体大概就是$E_8\times E_8$强耦合杂交弦,这玩意儿我们考虑$M$理论用$S^1/\mathbb{Z}_2$的紧致化实现,会出现两个End-of-world brane。有效拉氏量长下面这个样子:
\[L=\frac{1}{2\kappa_{11}^2}\int_{M_{11}}d^{11}x\sqrt{g}R-\sum_i\frac{1}{8\pi(4\pi\kappa_{11}^2)^{2/3}}\int_{M_i^{10}}d^{10}x\sqrt{g}|F_i|^2\]用CY3紧致化,积分到四维有效理论和四维引力以及YM理论(这里指的是$U1\times SU2\times SU3$标准模型在高能呢个表下的GUT)的拉氏量对比立刻得到:
\[G_4=\frac{\kappa_{11}^2}{8\pi^2\mathcal{V}d},\quad\alpha_{\mathrm{U}}=\frac{(4\pi\kappa_{11}^2)^{2/3}}{2\mathcal{V}}\]这里$\mathcal{V}$是CY3的体积,$d$是$S^1$的直径,或者说两个End-of-world brane的距离。这个理论和你单纯从弱耦合杂交弦的低能有效拉氏量,也就是十维超引力是不一样的:
\[L_{\mathrm{eff}}=\int d^{10}x\sqrt{-G}e^{-2\Phi}\left(\frac{4}{\alpha^{\prime4}}R-\frac{1}{\alpha^{\prime3}}\mathrm{tr}|F|^2\right)\]我们这里从$M$理论出发相当于考虑了非微扰的贡献,如果直接从十维超引力低阶相互作用出发,得到的是:
\[G_4=\frac{e^{2\Phi}\alpha^{\prime4}}{64\pi\mathcal{V}},\quad \alpha_\mathrm{U}=\frac{e^{2\Phi}\alpha^{\prime3}}{16\pi\mathcal{V}}\]然后根据$\mathcal{V}\sim M_U^{-6}$以及微扰弦的假设$e^{2\Phi}\ll 1$,得到Newton引力常数的bound:
\[G_4\gtrsim\frac{\alpha_\mathrm{U}^{4/3}}{M_\mathrm{U}^2}\]这个bound超过了现实世界真值,所以肯定是不对的,这被称为string unification problem,见文献10.1016/S0370-2693(97)00335-3。所以Witten想了个法子去考虑从M理论来的非微扰贡献,然后Witten来了一个重要的argue就是为了让$E_8$规范场的耦合不发散,必须要:
这个argue的细节我不太懂,但是后面的推导更无法说服我,Witten进行如下推导:
\[G_4\sim\frac{\kappa^2_{11}}{\mathcal{V}d}\gtrsim\frac{\kappa^{8/3}_{11}}{\mathcal{V}^{5/3}}\sim\alpha_U^2\cdot\mathcal{V}^{1/3}\sim\frac{\alpha_U^2}{M_U^2}\]虽然跟前面的版本相差不大但是好在这个时候真实世界在bound里面了,推导详细见文章hep-th/9602070。额,但是我自己的脑回路不一样,我是:
然后我想了下问题应该出在最后一个argue,也就是$d\sim M_U^{-1}$。从量纲上看这肯定是正确的,从物理上看如何说服我?我想到规范理论是长在膜上面的,所以膜之间的距离应当完完全全是个moduli,而且规范理论不同于引力,规范理论只能在膜里面传播,而引力可以超过膜在膜的横向上传播(参考膜世界理论)。所以$d$不能认为就由GUT能标决定。但是对于用于紧致化的CY3。由于他会直接作用到规范理论所在的空间,他整个是wrap在End-of-world brane上的,所以应当就完全由GUT的能标决定要紧致化到多小。这大概是为了说服我自己给的一个argue。。。
但是当今做高能物理的有多少文章不是在骗骗自己呢?突然想起来参加string-math的一天晚上和几个博后聊天,吐槽当今高能物理充满一堆不明所以的argue,就像是LQG算出来黑洞熵不对,但是argue差的一个常数倍不重要一样。。。
另外加了D膜非微扰项之后Dirac量子化条件也要修改,我也没大看懂,可以尝试继续看看hep-th/9609122。
2025-07-05
之前一直搞不懂在算D-brane的charge的时候是用几维球面去包裹,今天猛然发现是自己蠢到没边了。比如D3膜横向方向是$\mathbb{R}^6$,这不就可以看作是在6维时空中的一个点么。想一下三维时空中包裹一个点是用二维球面,自然到了6维就要用$S^5$去包裹。
今天看了以下李思老师对形变量子化的介绍:形变(代数)量子化简介
李思老师的个人网站上有个专门关于量子化的数学物理的讲义,前半截标准量子力学,后半截将数学物理,不过现在还剩下最后一章没写完,等一两年写完之后一定拜读拜读,一直对这部分数学物理比较感兴趣。不过或许我后面不会做这方面的研究,因为总觉得物理味太少。
首先就是从物理上讲量子化其实就是在谈Dirac的正则量子化的想法,用数学公理就是要找到一个算子$Q$把实数空间上的函数$f$,也就是力学量,变成希尔伯特空间上的算符$\hat f$,也就是可观测量算符。这个算符应当满足下面四条:
- $Q(1)=\hat 1$,且$Q$是$\mathbb{R}$线性的
- 把实函数变成一个自伴随的算符(厄米算符)
- $[\hat f,\hat g]=i\hbar\widehat{\{f,g\}}$
- 完备性
或者说我们就是在找$(A=\mathbb{C}[\mathbf{x},\mathbf{p}],\cdot)\Longrightarrow(A[\hbar],\star)$两个代数之间的同态,满足一些额外的性质。
对于搞物理的来说基本不会关注完备性,就一直这么用下来了。但是数学家惊人的发现,同时满足这四条公理的$Q$是不存在的!核心在于第三条和第四条互相完备!一般来说我们希望完备性仍旧成立,所以需要放宽第三条,物理上去想其实就是考虑$\hbar$的更高阶项的贡献,比如Weyl量子化,变完之后可观测量构成的代数的结合,或者说乘积,这里叫Moyal乘积长下面这个样子:
\[f\star g=fe^{\frac{i\hbar}{2}\left(\frac{\overleftarrow{\partial}}{\partial x}\frac{\overrightarrow{\partial}}{\partial p}-\frac{\overleftarrow{\partial}}{\partial p}\frac{\overrightarrow{\partial}}{\partial x}\right)}g\]对易子长下面这个样子:
\[f\star g-g\star f=i\hbar\{f,g\}+\frac{(i\hbar)^3}{24}f\left(\frac{\overleftarrow{\partial}}{\partial x}\frac{\overrightarrow{\partial}}{\partial p}-\frac{\overleftarrow{\partial}}{\partial p}\frac{\overrightarrow{\partial}}{\partial x}\right)^3g+\cdots\]把这么一个想法进行推广,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对原先经典的多项式环,或者说力学量构成的代数形变,这里参数$\lambda=i\hbar$,$\mu$是双线性算子:
\[a*b=a\cdot b+\sum_{k=1}^\infty\lambda^k\mu_k(a,b)\quad\forall a,b\in A\]这个代数会自然给出一个对易子结构,我们显然希望在$\lambda\to0$的时候回到原先的Dirac量子化第三个条件,也就是说这个形变推广就是加了一些高阶项:
\[\{a,b\}:=\lim_{\lambda\to0}\frac{1}{\lambda}\left(a*b-b*a\right)\]更有趣的是我们前面经典力学量代数$\mathbb{C}[\mathbf{x},\mathbf{p}]$可以换成一般的Poisson流形(比辛流形更广,辛流形要求一个闭的非退化二形式,而Poisson流形要求一个Poisson括号结构,显然一个辛流形一定是Poisson流形但反过来不一定)上的光滑函数$\mathbb{C}^{\infty}(M)$,然后同样去做形变量子化,只是这个时候$\mu$我们要求是由流形上的线性微分算子给出的(这在物理上相当于要求我们希望整个理论是local的),比如Weyl量子化就是这样的例子。形变之后$\star$就给出了一个$\mathbb{C}^{\infty}(M)[[\lambda]]$上的结合但不一定交换的乘法结构。
然后数学家第一句话就会去问在任何一个Poisson流形上是否总存在这样的形变,DeWilde-Lecomte-Fedosov-Kontsevich分别用不同的工具给出了「是」的答案。(事实上前三个人只说辛流形上是对的,最后一哥们用二维量子场论构造了Poisson流形上的结构)
另外这玩意儿其实和代数指标定理也有关系,这涉及到考虑如下的迹映射:
\[\mathrm{Tr}:C^\infty(M)[[\lambda]]\to\mathbb{R}((\lambda)),\quad \mathrm{Tr}(f\star g)=\mathrm{Tr}(g\star f)\]你可能觉得这样一个$\mathrm{Tr}$的定义很多余,那是因为你总是把$f,g$这俩玩意儿堪称希尔伯特空间上的算符或者说矩阵,别忘了,当我们这么看的时候其实是暗含指定了$C^\infty(M)[[\lambda]]$的某个表示,但是回顾我们前面讨论形变量子化,完全可以就单纯的讨论某个结合代数的形变,根本没必要涉及到任何一个具体的希尔伯特空间,然后涉及到上面的算符(当然Dirac量子化条件本身涉及到了这一点,不过上面说了可以抽象为代数的同态)。
可以证明辛流形上这个映射是存在且唯一的,而且真空配分函数完全由下面指标给出:
\[\mathcal{Z} = \mathrm{Tr}(1)=\int_Me^{-\omega_\lambda/\lambda}\hat{A}(M)\]$\omega_\lambda$和形变量子化有关,在$\lambda\to0$时回到辛形式,而$\hat A$是一个示性类,是纯几何的量A-hat genus in nLab。有关更多代数指标定理请见原始神作:
https://doi.org/10.1007/BF02099427
2025-07-06
以前一直觉得苹果这个“快捷指令”莫名其妙,今天有个需求是把原来apple ID的apple music上面的音乐全部添加到新的apple ID资料库。可能你想到的第一个方法就是先把所有音乐添加到一个播放列表,然后分享播放列表。但是这样只能把播放列表添加到资料库,里面的歌曲还是没有添加到资料库。而快捷指令可以创造workflow,所以他可以实现从播放列表中获取歌曲,然后把歌曲一个个添加到播放列表。这样一个简单的for循环结构编程就可以直接在快捷指令里面迅速实现。然后花了十分钟这六百多歌曲就自动添加到资料库里了。
但是不可否认我依旧觉得苹果某些事情上是畜生,为啥不能考虑到转换apple ID的要求做一个功能。毕竟苹果畜生到图书和apple music之类的是自动登录app store上面的账号,而不能单独设置账号登录。。。
2025-07-07
今天算D维施瓦西黑洞事件视界半径一个因子老是对不上,花了俩小时查论文才完全搞懂,这里记录一下。
D维黑洞的Schwarzschild解长下面这个样子:
\[ds^2=-hdt^2+h^{-1}dr^2+r^2d\Omega_{D-2}^2, \quad h=1-\left(\frac{r_\mathrm{H}}{r}\right)^{D-3}\]其中事件视界是拓扑球面(高维黑洞解事件视界拓扑可以是环面,比如black ring),半径为:
\[r_{\mathrm{H}}^{D-3}=\frac{16\pi MG_D}{(D-2)\Omega_{D-2}},\quad \Omega_n=\frac{2\pi^{(n+1)/2}}{\Gamma\left(\frac{n+1}{2}\right)}\]类似四维黑洞的推导,关键在于意识到$r\to\infty$时退化为球对称物体的牛顿引力:
\[g_{tt}\sim-(1+2\Phi)\]然后你就只需要把上面的$h$和这个对一下就好了,关键在于高维情况下$\Phi$是多少,你可能脑子里面想到的第一个办法就是用Gauss定理在高维推广去做,然后你会很快地发现有个系数对不上。翻开文献arXiv:0801.3471开头你就会看到标准的式子:(有点符号滥用,因为我是直接抄的文献上的式子,懒得改了,下面公式里面的$d$应该理解为时空维数,也就是前面的$D$)
其实这源于弱场近似,在平直时空微扰下引力场方程为:
\[\square\bar{h}_{\mu\nu}=-16\pi GT_{\mu\nu},\quad g_{\mu\nu}=\eta_{\mu\nu}+h_{\mu\nu}\]其中选定记号和规范:
\[\mathrm{e~}\bar{h}_{\mu\nu}=h_{\mu\nu}-\frac{1}{2}h\eta_{\mu\nu},\quad \nabla_\mu\bar{h}^{\mu\nu}=0\]无穷远处非相对论极限下把黑洞看作是一个点粒子,不过旋转黑洞可以带角动量,能动张量长下面这个样子:
\[\begin{aligned}&T_{tt}&&=\quad M\delta^{(d-1)}(x^k),\\&T_{ti}&&=\quad-\frac{1}{2}J_{ij}\nabla_j\delta^{(d-1)}(x^k)\end{aligned}\]求解场方程立刻得到:
\[\begin{array}{rcl}h_{tt}&=&\frac{16\pi G}{(d-2)\Omega_{d-2}}\frac{M}{r^{d-3}},\\h_{ij}&=&\frac{16\pi G}{(d-2)(d-3)\Omega_{d-2}}\frac{M}{r^{d-3}}\delta_{ij}\\h_{ti}&=&-\frac{8\pi G}{\Omega_{d-2}}\frac{x^kJ_{ki}}{r^{d-1}}\end{array}\]唯独重要的就是这个$h_{tt}$,他直接告诉我们$r_H$。我们发现直接弱场近似下解场方程就行了,然后再根据$g_{tt}\sim 1+2\Phi$倒推便可以得到高维牛顿引力势能公式。多说一句,有人曾经问我施瓦西解里面为什么事件视界面积和质量相关,那个公式是怎么来的。再解施瓦西解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先解$r>r_H$处球对称的真空解,这个时候$r_H$是当作一个积分常数来的,但是你别忘了解方程最重要的是边界条件处理,而黑洞质量就告诉我们他的能动张量就告诉我们边界条件是什么,所以可以定下来$r_H=2GM$。
2025-07-08
说起来就他妈来气,一个saddle point近似我搞了大半天结果毫无进展,这BBS一个参考文献也不放一个,真他妈觉得读者手撕合流超几何函数不难对吧😅😅😅
大抵是这样的,计算黑洞微观态涉及到对下面的配分函数计算:
\[G(w)=\frac{1}{16}\prod_{m=1}^\infty\left(\frac{1+w^m}{1-w^m}\right)^4=\sum_{N=0}^\infty\Omega(N)w^N\]而$D=5$的D1-D5-P黑洞熵等于:
\[S \sim \log \Omega(N),\quad N=Q_1Q_5 n\]由于上面的推导是在弦论里面得到的,为了和弱耦合下的超引力里面的结果比对,所以需要考虑$N\to\infty$。用围道积分就可以写作:
\[\Omega(N)=\frac{1}{2\pi i}\oint\frac{G(w)dw}{w^{N+1}}\]计算这个围道积分可以用鞍点近似,鞍点在$w=1$处,这附近$\Omega(N)$有如下的渐进行为:
\[G(w)\to\left(-\frac{\log w}{\pi}\right)^2\exp\left(-\frac{\pi^2}{\log w}\right)\]这个倒是easy的,因为这玩意儿在环面配分函数计算里面玩烂了,表示成模形式然后用现成的渐近公式就好了。但是不解的是BBS直接说得到:
\[\Omega(N)\sim(Q_1Q_5n)^{-7/4}\exp\left(2\pi\sqrt{Q_1Q_5n}\right)\]然后我搞了半天也不知道怎么搞出来,这个时候我又想起来了第二章的时候我也被BBS坑过一次,那里涉及到Hagedorn temperature的计算,或者说去问玻色弦某一质量激发态的个数在大N极限下的行为:
\[\Omega(N)=\frac{1}{2\pi i}\oint\frac{\mathrm{tr}w^N}{w^{N+1}}dw,\quad \begin{aligned}\operatorname{tr}w^N=\prod_{n=1}^\infty(1-w^n)^{-24}\sim\exp\left(\frac{4\pi^2}{1-w}\right)\end{aligned}\]上面这个渐近性是不难的,可以直接从Dedekind函数的渐近行为分析而来,要命的是为何代入围道积分后直接就得到:
\[\Omega(N)\sim N^{-27/4}\exp(4\pi\sqrt{N})\]然后我翻到我这一页做的笔记,果然写了一个大大的不解,就这俩问题搞了我一下午查了各种资料问了MMA问了AI都没有给出我类似的答案,关键是BBS上面还没有参考文献(黑洞的那个有,我看了下计算用的是Cardy公式,和这里似乎不太一样,而且结果是不含来自弦论的对数修正的,不过我只是粗略的看了一下,这个技术细节就先放在这里吧)。希望哪天能把这俩技术细节搞清楚。
2025-07-11
配分函数近似的技术细节依然困扰着我,BBS算弦论对黑洞熵修正公式的时候,考虑F弦的高质量激发态自发坍缩形成的黑洞。直接数杂交弦的BPS态得到:
\[d_N\approx16\hat{I}_{13}(4\pi\sqrt{N})\]这个$I$是第一类修正Bessel函数,书里面给出的定义是:
\[\hat{I}_\nu(z)=\frac{1}{2\pi i}\int_{\varepsilon-i\infty}^{\varepsilon+i\infty}(t/2\pi)^{-\nu-1}e^{t+z^2/4t}dt\]然后BBS口算得到$N\gg 1$时
\[S=\log d_N\approx4\pi\sqrt{N}-\frac{27}{2}\log\sqrt{N}+\frac{15}{2}\log2+\ldots\]但是这前面的几个系数我死活对不上,首先$I_\nu$的渐近展开长这样:
\[\mathrm{I}_{\nu}(z)\sim\frac{\mathrm{e}^{z}}{\sqrt{2\pi z}}\sum_{n=0}^{\infty}\frac{(-)^{n}(\nu,n)}{(2z)^{n}}+\frac{\mathrm{e}^{-z+\left(\nu+\frac{1}{2}\right)\pi\mathrm{i}}}{\sqrt{2\pi z}}\sum_{n=0}^{\infty}\frac{(\nu,n)}{(2z)^{n}}\]对于$z\in\mathbb{R}$的特殊情况只有前面那一项,因为后面的是虚数项,这里使用了记号:
\[(\nu,p):=\frac{\Gamma(1/2+\nu+p)}{p!\Gamma(1/2+\nu-p)}\]MMA其实是可以直接计算这个展开的,给出的结果是:
\[\hat S \sim 4\pi\sqrt N+\frac{1}{2}(5\log2-2\log\pi-\log\sqrt N)+\mathcal{O}\left(\frac 1z\right)\]唯一可能的就是书里写的$\hat I$和MMA里面的,或者说王竹溪特殊函数概论里面的那个$I$有所差别。我没有找到类似的积分定义式来说明这一点,所以目前我还不知道如何说明修正项的系数不一致问题。我也懒得为这个技术细节浪费时间再去详细找答案了,感觉BBS黑洞前面三章讲热力学和熵公式之类的讲的还蛮好,技术细节点到为止,到后面着实是有一点潦草了,整个最后一小节就没看大懂。
2025-07-13
AdS/CFT以及弦论中的黑洞构造都需要用D膜(或者更广泛的说NS膜或M膜之类的也可以)来构造带事件视界的几何,两个地方用到的有点细微的差别。一般谈黑洞我们希望谈四维五维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希望背景时空是CY紧致化之后的,然后黑洞存在于internal的CY流形上,wrapped在上面。不过AdS/CFT那里,我们更多叫black-brane解,这个时候膜并不是wrapped的结构,而是flat空间上无限延伸的结构,背景时空也是完整的十维时空,整个几何是渐近$\text{Mink}_{1,9}$的结构。所以两者首先在求解时用的有效场论就不一样,black brane那里没有紧致化,所以只是低能情况下的十维超引力。而黑洞那里由于维数约化了,所以internal CY那部分就只剩下零模了,激发态给砍掉了,得到的是四维五维超引力($\mathcal{N}$取决于CY流形)。另外由于场论不一样膜上面带的荷也就不一样。black brane这里是标准的R-R荷,但是黑洞因为维数约化,从超引力就能看到他会带更多的$U(1)$的荷,比如五维是$27$个$U(1)$的荷,最少也是用三个荷给出D1-D5-P构造,相当于对角化标准基底,剩下的用S、T、U对偶这些联系。最后当然最直观的就是几何的区别,黑洞解都是只写external的部分,因为internal的被挡在事件视界里面,但是black brane解都是完整的十维的解,而且有紧致化的时候类似的warp几何的形式。
2025-07-15
今日和高中同学再次聚餐,这已经是暑假第二次聚餐了,马上也会有第三次。但来的人越来越少,每次的聚餐会都是对老友的送别会。大学毕业了,我至少还会在学校里待五年,但有的同学本科毕业就打算工作(虽然现在就业形势非常紧张,但是找到了还算不错的工作)。有的同学打算继续读研,这也是大多数人的选择,不过读博的概率自然是非常非常低。时光真的飞快,小学时候的同学都要工作了,想起来小学时候老师让我们写十年之后大家的变化,可惜当年的作文纸搬家弄丢了,我也不记得当初梦想的同窗好友的未来生活了。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虽然我从未觉得剧本杀很有意思,看电影也当然能一个人看50G的原盘版本,但是和老友们一起做这件事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之后大家真的也要离开这个小县城,而且不当老师还没有寒暑假,相聚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人也越来越不齐了。在小县城的我们至少过年回家还能相聚,毕竟根在这里,而大学同学,那只能感谢互联网还能让我们联系了。但是当老友之间生活上渐行渐远,口中的话题越来越少,大家都忙于拼搏自己的梦想,或许后面就算是十几年的朋友之间联系的也越来越少吧。
不过转念一想,这不是恰恰再说明大家都在奔向更好的生活吗?正说明大家一直都在朝前走而不是原地踏步。所以分别确实得辩证地看作是大家崭新的开始,这也是恰恰作为朋友的我最愿意看到的。
2025-07-16
\[S=\int d^4x\mathrm{~Tr}\left(-\frac{1}{4}F_{\mu\nu}F^{\mu\nu}-\frac{1}{2}(D\Phi_I)^2+\frac{i}{2}\overline{\Psi}D\Psi+\frac{g}{2}\overline{\Psi}\Gamma^I[\Phi_I,\Psi]+\frac{g^2}{4}[\Phi_I,\Phi_J]^2\right)\]这是四维的$\mathcal{N}=4$的SYM理论,可以用十维SYM维数约化得到,也可以用D膜的世界体上的场论解释(或者说来源于此),$A_\mu$是世界体内部的规范玻色子激发,$\phi$是横向的collective coordinate。这俩都是无质量激发态,都在$U(N)$的伴随表示里面,上面带的指标不同只是因为D膜的存在把十维庞加莱对称性破缺成了四维庞加莱和六维旋转对称性,所以产生湮灭算符所处的庞加莱群的factor不同导致他们处于庞加莱群的不同表示,所以一个是四维矢量规范子一个是四维标量场。而$\phi$的$SO(6)$R对称性一下子就能解释成D膜缺陷没有破坏的那六个横向维度的对称性。
很有意思的是杜老一直在做的是Yang-Mills-Scalar理论,我突然想起来他就是$\mathcal{N}=4$ SYM的玻色版本,也就是直接把费米子砍掉得到的,此事在Polchinski第一卷中亦有记载。那么作用量就是:
\[S=\int d^4x\mathrm{~Tr}\left(-\frac{1}{4}F_{\mu\nu}F^{\mu\nu}-\frac{1}{2}(D\Phi_I)^2+\frac{g^2}{4}[\Phi_I,\Phi_J]^2\right)\]2025-07-19
今天看AdS/CFT的时候突然看到D膜的Mayer效应,这玩意儿第一次看没看懂,现在依旧懵逼。我大概只能get到naive你会想Dp膜只能耦合p+1的form,毕竟你看type II超弦都会跟你说稳定的BPS D膜就是根据II型弦论里面存在的的form field来的。但是实际上D膜作用量是完全可以包含低维的form的,来自于chern simons项的贡献。不过如果考虑的背景时空是平凡的,也就是没有flux也没有B field之类的,这一项会退化到只有p+1 form。
but和其他维数form field耦合意味着会带其他维数的RR charge,那这个时候D膜还是BPS的吗?应该如何理解这个时候的D膜?目前我还没搞太懂,不过D膜本身我也没太搞清楚,需要等我看专门讲D膜的那本书之后再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理论还有各种各样的膜,S对偶产生的NS膜,还有紧致化来的KK膜之类的,所以这个坑挺深的,目前了解几乎为0)
2025-07-20
今天看了周稀楠老师关于CFT中的自举法的科普文章DOI:107693/wl20250603。明白了一件事情,我之前关于CFT的numerical bootstrap的argue是对的。大概是几个月前我曾尝试去follow Ising model用CFT自举去算临界指数,那个时候数值计算得到的可行域是在一个折线以下,也就是说边界是一个光滑曲线除了在一点处有kink,由于数值计算只是告诉你自洽的可能的理论取值范围,自洽并不代表是真正的理论,而我看文章当时argue这个kink这里就是真正的理论。毕竟你可以想象由于这里存在一个真正的理论,所以自然他周边的理论就很难去被排除,所以会出来一个尖点。我当时没有继续去细细追究文献,认为这个地方或许只是一个猜测而已,现在来看我想的是对的,这玩意儿确实当时是猜出来的,只是二维的我们有严格解,知道值刚好就在尖点计算值那里。三维的后来用蒙特卡洛模拟也能发现刚好就在尖点那里。不过后面进一步加了更高阶的自举方程用自洽性完全把可行域缩小到了尖点附近一个非常小的范围内,这也说明了确实尖点处就是正确的理论。这套自举方法相比于传统蒙特卡洛模拟最大的好处可能是自举算出来的都是严格的,因为自举方程是严格的,后面的计算都是用线性规划算法去算的,但是蒙特卡洛毕竟还是一个概率算法,就像是用蒙特卡洛计算圆周率如果你精度不高是完全可能算出来3.2的,而且就算精度提高了那误差也是不可消的。
2025-07-21
今天把BBS彻底看完了,本来预计前两天就该看完的,不过中间摆烂休息了几天,后面或许会抽些时间看一看习题。对这本书评价我觉得一半是专业书籍,而一半如果你只看BBS本身,那么就纯纯的科普文。如果你跟我一样,非常执着于技术细节,希望书本至少跟polchinski第一卷一样有非常详细的推导,那么你非常不适合看这本书,我看这本书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难受,特别是后面几章。弦紧致化的那部分我觉得如果你不看原始文献根本看不下去。略去技术细节的好处就是会让你在600面的书里面塞下上千页的信息量,你看完之后会对弦理论整体有个大致的感觉。那么代价呢?你会在看这本书的某些段落时,只是一个个名词在眼前闪过,完全不知道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来的。如果你不是跟我一样在学习这本书之前先看过一遍polchinski第一卷,并且做弦振幅相关的毕业设计把第一卷相关部分又看了一遍,超弦部分看过施罗德和黄晨的讲义熟悉过RNS超弦振幅的计算(至少从SCFT出发,如果你会blumenhagen教材上面的bosonization那一套当然更好),那可能你看完这本书之后算个三快子振幅都会卡壳半天。这本书对技术细节本身的省略可谓是省之又省,当然这也意味着这本书本身的阅读门槛不高,如果你不追求第一遍就对弦论的技术细节有比较详细的了解,或者说你本身今后并不做hardcore的弦论,只想知道自己做的一些问题的弦论背景,那么这本书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而且这本书是非常新的书,目前市面上的经典弦论书这本最新了,而且由于BBS本身就做了很多弦唯象的工作,所以这部分相对来讲是讲的比较多的。
另外晚上看完了疤面煞星,其实存在电脑里面很久了,一直没抽出时间看,今天新耳机到了借着试试耳机就给看了。传统黑帮片套路,小人物被赏识崛起,然后做大做强丢失自我,最后众叛亲离孤独死去,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2025-07-23
今天又工作了一整个晚上,睡前整理了一下这二十天来学的一些东西,虽然看似达到了甚至超出了本月初我的预期,但很多地方我都觉得学的不扎实。大学四年似乎一直在学习,现在申请结束了我依然没有找到让我休息的理由,内心感觉休息就是在犯罪。但是仔细一想我这样学也没有什么作用,人类就是会遗忘,就算是我写了详细的笔记并且在讨论班讲过的CFT和拓扑序我照样过一两个月忘得干干净净,只有一些经常作为工具使用到的一小部分会记得个大概。所以如果不去做某方面的科研,从功利主义上看学这方面相关的知识都是徒劳。如果我是tenure或者我可以美其名曰培养学科素养各方面都学学,可是作为学生我没有这样的无限的时间。现在我想做的就是广撒网,通过各个方向的研究都浅浅看过,来找出自个真正的研究兴趣。目前我看完了BBS,但是或许是我对弦论理解的还并不深刻,看过的资料不多,目前还没多大的想法。希望在杭州暑期学校回来过后我能找到自己想要的归宿。
最初黑洞热力学确实仅仅只是建立在类比上面的,后面Hawking证明黑洞确实会对外有黑体辐射才确立了黑洞确实是一个热力学物体。今天猛地回忆起来著名的Wald公式,对任意的Einstein-Hilbert形式的作用量:
\[S=\frac{1}{16\pi G_N}\int d^4x\sqrt{-g}(R+\mathcal{L}_{matter})\]可以写下对应黑洞解的熵公式:
\[S=-2\pi\int_{\Sigma}d^2x\sqrt{-h}\frac{\delta\mathcal{L}}{\delta R_{\mu\nu\rho\sigma}}\epsilon_{\mu\nu}\epsilon_{\rho\sigma}\]而这玩意儿你带进去算会发现恰好得到的就是Bekinstein-Hawking熵公式:
\[S=\frac{\mathcal{A}_h}{4G_N}\]很有意思,不论你黑洞长啥样,最后都会归结为这么简单的一个公式
2025-07-25
今天终于看完了刘洪老师的全息原理课程,这是继毛子的Moorse理论课程之后看过的第二个网络课程。另外,似乎我了解到国内SIMIS有给研究生开量子力学证明Moorse理论,虽然这个证明之类的确实很妙,完全可以作为欣赏去学习,不过如果跟毛子一样单纯只讲这玩意儿的证明似乎没多大的实用价值。如果是跟David Tong的超对称量子力学lecture一样,并非特别关注这玩意儿的严格证明,而是更广泛的关注非常有意思的数学物理玩具模型——SUSY QM,我倒觉得是很好的。
话说回来,刘洪老师这个课程相对来讲还是非常非常基础的,感觉是面向高年级学过一点QFT本科生的课程,课程设置并不难(但是习题还是很有意思,有一些还是很有难度的)。总共课时四十个小时,从黑洞热力学一路讲到全息纠缠熵,计算细节也点到为止,但不至于跟BBS一样完全没有。加上看刘老师讲义和写笔记的时间我估计在这门课上实际花费六七十个小时,最终写了份一百多面的笔记(等关于这门课的blog整理个大概之后再把这笔记挂网站上),有些技术细节刘老师上课没展示的我也进一步参考别的资料补全了。可惜的是这门课到全息纠缠熵这一高潮就戛然而止了,课程推进的一直很慢,到后面刘老师才加快脚步,如果这门课能多讲四五节讲到QGP这些唯象方面或者其它方面的应用那就更好了。不过我最近也开始看User Guide了,看目录很适合作为这门课的补充进阶阅读资料,大概八月底会读完,到时候我再来评价。
尽量八月初把刘老师这门课的核心整理以下挂网站上,希望月底不会鸽。。。(因为最近发现荒野大镖客很好玩)
2025-07-29
甚疲,今日睡了一整天(上一次觉得这么累还是疫情时候卧病在床,隧想记录一下),好消息是日本导师向我发来邮件告知我入学前一周组内会有团建,而且能用他的经费资助我的旅行。火速改掉机票,希望后面一切顺利。
另外我似乎对F-string和D-string的理解一直有问题,我之前以为这俩的区别是能否和R-R flux耦合,似乎F-string可以和R-R flux耦合,而且这是AdS超弦无法用RNS处理的核心问题,AdS时空中必定是要有膜带来的R-R charge的,不然背景时空运动方程不自洽。但是F-string的耦合并非和D-brane一样通过Chern-Simons项带来的,本质区别就是F-string虽然耦合但是不作为flux的源存在,他自己不像D-brane一样携带R-R荷。
不过更关键的地方可能是两者的贡献不一样,F弦是微扰的贡献,而D弦和D膜一样来源于孤子解,一定是非微扰的物体,对理论的贡献是指数形式的,不过我还真的完全不理解D膜为啥就是孤子解,希望在杭州的时候能碰见人给我解释解释。
2025-07-30
今天继续学AdS/CFT,里面有个重要的应用是hydrodynamics。之前总听到这个词,一直以为是跟流体相关的,现在发现流体只是这玩意儿的一个重要例子罢了。我们谈论一个系统是hydrodynamics的,是说我们在用一个有效理论描述这个系统的宏观行为,比如热扩散,当我们不关注体系的微观结构的时候,宏观量的描述就是用Fourier定理以及Fick定律。这些方程里面就会涉及到一些扩散系数,本身来源于我们忽略掉的微观自由度(从统计物理的角度看是线性响应理论久保方程里面格林函数给出来的)。所以流体的NS方程显然是完全不关心流体分子之间的相互碰撞,而是直接从宏观的角度去分析流体运动,所以可以看作是hydrodynamics的一种,只要是我们在用有效理论描述体系的宏观行为,我们关注的可以是相变点附近的序参量的变化,也可以是扩散模型里面由守恒流推动的守恒荷的扩散行为,这些体系微观都很复杂,而当我们仅仅关注其宏观量变换忽略微观作用细节时,往往方程都会被打包成一个较为简洁的形式,这就叫做一个hydrodynamics。
hydrodynamics大家比较关注的是里面的守恒荷和守恒流,因为守恒方程告诉你 $\vec{q}\to 0\iff \omega\to 0$,这也叫做hydrodynamics极限,所以大家在利用Kubo公式分析流荷关系之中的系数的时候,最后还原到与格林函数之间的关系都会取这个极限,也就是长波低能极限,这是hydrodynamics的特征,但是我目前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个极限,我以为只是守恒方程的一个必要性而存在。特别是我很惊讶于用线性响应理论这种完全看似是量子统计的工具去计算流体力学里面的粘度这种看起来完全是宏观的问题。计算电导率之类的我都还比较好接受,或许是流体力学也能看作是有很大的分子动力学微观起源吧。
另外书上多谈了些关于流体力学的例子,我以前是修过流体力学的(为了备战CUPT学的,可惜后面也没怎么用上),可惜都还给老师了,只隐隐约约记得一个动力学NS方程和静力学Euler方程,怎么推导的完全记不清了。全息原理的书上是从相对论流体守恒方程出发然后非相对论极限得到的。里面得到了非相对论粘性流体的运动方程:
\[\varepsilon(\partial_0+\nu^j\partial_j)\nu^i+\partial^iP-\eta\partial_j^2\nu^i-\left(\zeta+\frac{1}{3}\eta\right)\partial^i\partial_j\nu^j=0\]然后根据流体不可压缩性argue可以把最后一项给干掉,因为不可压缩对应能量密度$\epsilon$常数,然后连续性方程给出$\partial_i v^i=0$。这一步没看太懂,我知道无粘流体这个结论成立,但是对于有粘的我不太确定,不过这玩意儿似乎不太重要我就懒得去查证了,总之最后有NS方程:
\[\boxed{ \varepsilon(\partial_0+\nu^j\partial_j)\nu^i+\partial^iP-\eta\partial_j^2\nu^i=0 }\]改天我哪天想起来了再看看流体力学,显然这部分内容更重要的是对线性响应理论和格林函数的理解。因为AdS/CFT有个很重要的应用就是他也有类似的荷流共轭性boundary上的算符对应bulk里面的流,然后把boundary上面的配分函数取个sourced微扰,source对应其在bulk里面流的在boundary上的边界条件。然后GKPW字典告诉你两边配分函数一样,然后一个神奇的结果就是刚好就会出现线性响应久保公式:
\[G_{E}(k):=\left<O(k)O(-k)\right>_{\phi=0}=\frac{\left<O(x)\right>_{\phi}}{\phi(k)}\]而boundary上的关联函数我们是知道怎么用witten diagrams计算的,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如何用bulk里面的信息完全重构出boundary上面的格林函数,而这恰恰是线性响应里面最重要的,线性相应理论告诉你sourced或者说非平衡的信息可以完全由平衡态,也就是$\phi=0$的关联函数的信息提取出来(线性阶如此)。但是如何求解这个关联函数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很多时候人们就是在发明新的方法工具求解这个格林函数,而AdS/CFT就给了这么一种方法,但我觉得肯定这不是主流,我觉得这些人用全息用的过于随意,各种鞍点近似加上奇怪的CFT与AdS之间的对应,我觉得这不好,算出来的结果可信度非常低。不过我这一个月学的全息除了从弦论书上学的top-down的构造,剩下的基本都是这种东西了,top-down的构造是从弦论来的非常严谨的猜想,但是其研究难度极大,难度在于大家根本不知道AdS弦的作用量怎么写(RNS无法告诉你如何与R-R flux耦合,而GS作用量又极其复杂且有问题)。这种below-up的东西研究门槛确实低了不少,但原因就是大部分人根本不懂这玩意儿怎么从弦论来的,而是一昧的不断向其中加入自己看起来能推导出正确结果的假设,然后去做。这就很无聊了。。。。。
2025-07-31
月末,总结一下完成与未完成之事,希望未完成之事都能在下个月完成。这个月总体工作状态我还比较满意,但是有一些地方因为我的懒惰最终没有完成。
- 首先是BBS读完了,这个本来我是预计八月初才完成的结果提前了十多天,但是没有完成BBS的习题,也是希望八月能零散做一些。
- Witten的广义相对论的文章我读了前面六章,还差拓扑监督那里没有读完,其实是可以一口气读完的,不过我发现之前读的太快没有仔细品味这个非常有意思的领域,而且我短时间内应该不能依此写一篇笔记出来,所以就先暂停了,后面我肯定会抽空写一点关于经典广义相对论这些漂亮结果的一些看法。希望在八月中从杭州回来之后着手完成
- 刘洪老师的讲课录像看完了,但是blog没有按时完成,因为我写完大N展开之后觉得或许需要等我看完AdS/CFT对全息有个更好的理解之后再写,希望八月底能按时完成。
- AdS/CFT user guide看完了前九章,在去杭州前应该能看完前十章,看得非常快,因为不少内容是刘洪老师的lecture里面已经讲过的,不过看一遍书我的理解确实更深刻了一些。
- 代数拓扑最后一章没有按时读完,不过八月回来后应该能很快完全读完。
- 黎曼曲面没有按时读完,因为我发现这部分内容我暂时应该用不到,所以就先搁置了。
- 日语目前进度比我预想的慢了一点,大概慢了十天的进度,不过目前计算应该能在去日本之前学完初级2,頑張ってください!
希望去杭州的暑校能学到不少新东西!结交不少新朋友!
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2025年7月の手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