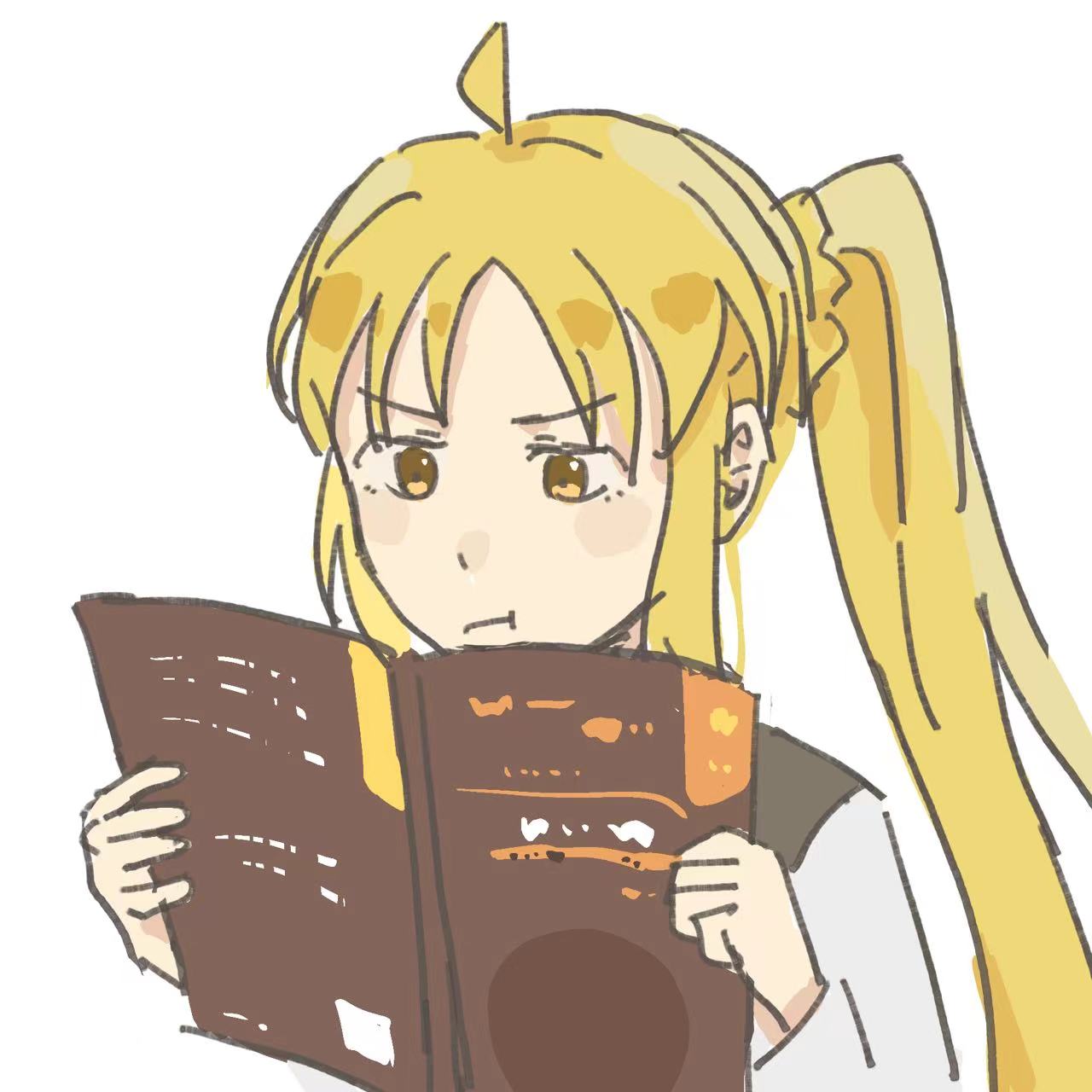由于日语八月份欠了不少债,所以这个月基本都在学日语,终于赶在入学前学完了大家的日本语初级。不过来到日本之后发现还是听和说完全不懂,还需要加油练习。九月底来日本之后由于也没个固定居所(这又不得不提傻逼宿舍十月一日报道当天才能入住而且无法帮我寄存行李这个傻逼规定了。。。),所以就趁着这点时间在东京瞎几把晃悠了一下。
9月1日至9月6日在湖北老家学习
2025-09-02
最近一直在写介绍pure spinor的报告,查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早在2002年,Berkovits就给出了有质量第一激发态的无积分顶角算符:hep-th/0204121
但是直到2018年,才算出满足$Q_B U=\partial V$的积分顶角算符:1802.04486
然后感受一下这恐怖的公式压迫感:
\[\begin{aligned} F_{mn}&=-\frac{18}{\alpha^{\prime}}G_{mn}\quad,\quad F_{m}^{\alpha}=\frac{288}{\alpha^{\prime}}(\gamma^{r})^{\alpha\beta}\partial_{r}\Psi_{m\beta}\quad,\quad G_{m\alpha}=-\frac{432}{\alpha^{\prime}}\Psi_{m\alpha}\\F_{mpq}&=\frac{12}{(\alpha^{\prime})^{2}}B_{mpq}-\frac{36}{\alpha^{\prime}}\partial_{[p}G_{q]m}\quad,\quad K^{\alpha\beta}=-\frac{1}{(\alpha^{\prime})^{2}}\gamma_{mnp}^{\alpha\beta}B^{mnp}\\F^{\alpha}{}_{\beta}&=-\frac{4}{\alpha^{\prime}}(\gamma^{mnpq})^{\alpha}{}_{\beta}\partial_{m}B_{npq}\quad,\quad G_{mn}^{\alpha}=\frac{48}{(\alpha^{\prime})^{2}}\gamma_{[m}^{\alpha\sigma}\Psi_{n]\sigma}+\frac{192}{\alpha^{\prime}}\gamma_{r}^{\alpha\sigma}\partial^{r}\partial_{[m}\Psi_{n]\sigma}\\H_{\alpha\beta}&=\frac{2}{\alpha^{\prime}}\gamma_{\alpha\beta}^{mnp}B_{mnp}\quad,\quad H_{m\alpha}=-\frac{576}{\alpha^{\prime}}\partial_{[m}\Psi_{n]\alpha}-\frac{144}{\alpha^{\prime}}\partial^{q}(\gamma_{q[m)}^{\sigma}\Psi_{n]\sigma}\\G_{mnpq}&=\frac{4}{(\alpha^{\prime})^{2}}\partial_{[m}B_{n]pq}+\frac{4}{(\alpha^{\prime})^{2}}\partial_{[p}B_{q]mn}-\frac{12}{\alpha^{\prime}}\partial_{[p}\partial_{[m}G_{n]q]} \end{aligned}\]2025-09-05
今天晚上听了刘洪关于冯诺依曼代数以及其在spacetime emergency上的应用的讲座,隧记录如下。刘洪老师也提到他正在写关于这个的review,过一段时间应该会发在arxiv上,期待一下。另外,把做好的ppt发给了Yamazaki,但是Yamazaki告诉我假设大家都比较熟RNS超弦似乎不太行,但是我又不可能在讲pure spinor之前讲一下弦论是什么,因为pure spinor本身就很技术,不太容易把技术细节藏起来,也或许是因为我懂得不多,还不太懂演讲技巧。所以比较头疼二十天后怎么跟大家介绍。
这里的emergency重要的clue围绕纠缠熵来的,我们知道Ryu-Takayanagi给了我们很好的边界场论纠缠熵和bulk的对偶。但是这里面其实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对于场论这种自由度无限的体系,他的纠缠熵一般都是发散的,所以我们需要跟做重整化一样去做cut-off,从实践上看这倒没什么,但是从本质上看这不是一种根本性的解决手段。而这个根本性的解决手段其实就隐藏在我们如何去描述纠缠?那从物理上你可能就说无非就是一个态无法factorize,我们也很好从物理直观上告诉自己什么是子系统,然后总的希尔伯特空间是子系统的张量积,然后里面就会有一些态是无法factorize的,所以我们就叫做发生了纠缠。
但是这个描述依赖于一个数学上非常强的条件,就是希尔伯特空间必须是factorize的:
\[\mathcal{H}=\mathcal{H}_1\otimes\mathcal{H}_2\]也就是说我们要从数学严格定义什么是子系统,都需要依赖这个前提条件。对于一般的体系,这一点是不用怀疑的,但是涉及到无穷自由度的体系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微妙。举个例子,想象两条无穷长的平行的自旋链,两个自旋链之间每个对着的自旋相互发生纠缠,比如是下面的纠缠态:
\[\cos\theta\ket{\uparrow\downarrow}-\sin\theta\ket{\downarrow\uparrow}\]在$\theta=\frac{\pi}{4}$的时候发生最大纠缠。体系的总的希尔伯特空间是有限能量的激发态,这里有限非常值得琢磨,每对左右自旋之间相互作用发生纠缠,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对这整个系统作用一些算符,比如flip一些自旋来改变体系的能量,但是我们前面说过,我们考虑的希尔伯特空间是有限能量的态,那么肯定只能flip有限多个自旋,否则能量无限大了,而这直接意味着必定整个希尔伯特空间不是factorize的,否则,这个体系中一定会存在factorize的态$\ket{\psi}\otimes\ket{\phi}$。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把没一堆自旋都通过flip的方式解耦成没纠缠的态。这意味着我们要flip无穷多次,和我们的假设矛盾。同样的事情在格点场论在格距趋于$0$的时候变成连续场论同样会出现。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希尔伯特并非factorize这件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如果我们拒绝用引入cut off的方式来处理,我们就必须面对一个问题,这个时候下面的态再来描述纠缠就没意义了:
\[\sum_{i,j}a_{ij}\ket{\psi_i}\otimes\ket{\phi_j}\]回到前面说的,数学上麻烦的其实就是这个时候如何去描述子系统,我们可以通过直接来描述子系统从而描述纠缠,事实上这是可以的,而且可以通过所谓冯诺依曼代数完全刻画。
某个量子系统上的一个冯诺依曼代数$\mathcal{A}$是指其算符的一个子集,要求在下面的条件下封闭:
\[\lim_{i\to\infty}\bra{\psi}a_n\ket{\chi}=\bra{\psi}a\ket{\chi},\quad\forall \ket{\psi},\ket{\chi}\in\mathcal{H}\]
- 厄米共轭
- 算符乘积(复合)
- 矩阵元极限 前面两个没啥好说的,一个是幺正一个是代数闭的条件,最后一个意思是说如果一个序列$\{a_i\}\in\mathcal{A}$,而且下面的所谓弱极限存在:
那么一定也有$a\in\mathcal{H}$。
由此,我们不直接去描述子系统上面有那些态,转而去描述其上面有哪些操作,也就是算符。而子系统就由这些算符构成的一个冯诺依曼代数来描述。也就是说冯诺依曼代数描述了一个子系统,一个子系统也完全可以重新用冯诺依曼代数表述。自然,冯诺依曼代数也被认为是描述量子纠缠的语言。
冯诺依曼代数大致可以分为下面三类(刘洪老师没有给出reference,不过有观众指出在Haag写的Local Quantum Physics里面有讨论):
- Type I:这一类冯诺依曼代数一定对应的是factorizable的一个希尔伯特空间,也就是说一定有$\mathcal{H}=\mathcal{H}_1\otimes\mathcal{H}_2$,其中$\mathcal{A}=\mathcal{B}(\mathcal{H}_1)$,$\mathcal{B}$表示括号里希尔伯特空间上面的算符集合。进一步根据$\mathcal{H}_1$的维数可以分为$\text{I}_n$和$\text{I}_\infty$两类,这里$n=\dim\mathcal{H}_1$。
- Type II: 这一类冯诺依曼代数又可以细分为$\text{II}_1$和$\text{II}_\infty$两类。
- Type III: 这一类冯诺依曼代数可以细分为$\text{III}_1$,$\text{III}_{0<\lambda<1}$和$\text{III}_1$三类 注意,后面两类对应的希尔伯特空间都是non-factorizable的。
回到之前说的两个平行自旋链的例子,用$\mathcal{A}_L$和$\mathcal{A}_R$两个冯诺依曼代数表示左右子系统。那么我们可以得出对于$\theta=\frac{\pi}{4}$的时候,这两个冯诺依曼代数是type $\text{II}_1$的,对于$\theta\neq\frac{\pi}{4}$,这两个代数是type $\text{III}_\lambda$,这里$\lambda = \tan^2\theta$。另外可以严格证明对于相对论场论中的任何开集,对应的冯诺依曼代数都是type $\text{III}_1$。
从上面的例子就能看出冯诺依曼代数确实描述了纠缠,比如不同的纠缠就对应不同类型的冯诺依曼代数,不过这种描述是非常粗糙的,实际上可以用modular flow这种高级的代数工具去提取出冯诺依曼代数里面关于纠缠的更多的信息。另外最后说到了相对论量子场论的冯诺依曼代数具有一种一般性,我们可以argue或许是时空的连续性以及时空的因果性这种最基本最内在的表现导致了冯诺依曼代数必定会是这样unique的一类,当然这只是argue。
后面刘洪老师就基于冯诺依曼代数来讲其在spacetime emergency上的应用,不过这部分我听得有点迷,大致随便写写。
我们一般对时空的描述就是背景度规加上上面物质场的拉氏量,这个描述当然是非常成功的,他发展了一套量子场论。但是这套描述并没有manifest local physics,时空因果性以及entanglement structure。所以既然我们想本质的去描述时空从而谈其emergency,我们自然想找到一套manifest这些时空的更基本的性质的理论,这套理论就是代数量子场论。代数量子场论抛弃拉氏量这套描述,转而去考虑时空的开集上的算符以及算符之间的关系这套代数系统作为最基本的自由度。这套理论就能很好地刻画时空结构。比如考虑$O_1\subset O_2$,那么自然我们就要求$\mathcal{A}(O_1)\subset\mathcal{A}(O_2)$。如果$O_1$和$O_2$之间不是包含关系而是差的类空间隔,也就是说没有因果性,那我们自然希望$\mathcal{A}(O_1)$和$\mathcal{A}(O_2)$上面的算符互相对易。知道了这个,那么我们现在对时空emergency的描述就是如何去用boundary的信息重构出bulk里面的代数量子场论。
基于前面这一大段指导思想,刘洪老师讲了一下他的研究(with Leutheusser, 2022),也就是所谓subregion-subalgebra对偶,这套对偶的字典是把bulk的subregion也就是一个时空区域对偶到边界上的一个type $\text{III}_1$冯诺依曼子代数。如果两个时空区域包含关系,那么对应的冯诺依曼代数也是包含关系,如果是没有因果性,那么对应的冯诺依曼代数就互相对易。后面还提到了这里面的哲学实际上和Gelfand对偶是一致的。
最后刘老师举了个Thermal Field Double state的例子来说明这个对偶,不过我实在是没有听太懂。考虑两个边界一左一右CFT构成的$\ket{\text{TFD}}$态,在温度很低的时候对应的冯诺依曼代数在大N极限下依旧是type I,这个时候希尔伯特空间是factorizable的,对应的bulk里面的是两个互相纠缠的AdS时空,但是两个AdS时空是互不相连的。有意思的是在高温的情况下对应的冯诺依曼代数在大N极限下是type $\text{III}_1$的,这个时候对应的bulk理论并不是两个disconnected的AdS时空,而是一个虫洞几何。近年来围绕这个也发展了一些关于Algebraic ER=EPR的研究。
9月7日至9月22日在珠海家里学日语
2025-09-06
猛然想起来我计划看完弯曲时空量子场论,但是由于写ppt耽搁了,这本书即使是作为QFT读物阅读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这本书我去年这个时候就开始看了,一直看到现在也没看完,也就看完Unruh效应的分析,Hawking辐射的计算其实类似,也是找两个真空。不过后面我学的就是刘洪讲的TFD态的版本了,纠缠的意味更强一些。改天补完AdS/CFT笔记的时候把Hawking辐射的分析补上,后面应该不会大看这本书了,毕竟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而且凯子哥跟我说早在上个世纪,弯曲时空量子场论就差不多被抛弃了(当然也不可否认计算霍金辐射这些确实很妙,但是其存在的问题更多,而且不是technical是conceptual的问题)。。。这下看来更没有看的必要了,看来我还是更关注一下数学物理的学习吧。
2025-09-08
今天翻译完了辛几何日语书的第四章,主要讲的是各种各样辛几何的例子,不过从这一章就能看出此书写作非常随意了,有很多概念必须要自己查别的书,并非其导言上写的如此“closed”。另外这一章的typo也非常严重,我都查到了正确的公式进行更正。
最后一节简短地提到了辛流形在奇数维的类似物——切触几何。这个东西我在大二大三的时候就有所耳闻,起因是图书馆有一本卓里奇写的《自然科学问题的数学分析》(在翻译这一章的时候我还以为是Arnold写的,找了好久都没找到),里面有一个章节就简短地提到了切触几何和热力学可以联系起来,不过当时我的几何水平比较差,所以没有读一遍。今天翻译到这才突然想起来这么一回事。希望之后有空读一读这本书,虽然卓里奇数学分析无精力通读,这本小书还是应该能完整读下来的。
晚上看了会Yang-Hui He他们用Machine Learning处理Calabi-Yau流形那一套,看了点review。看不太懂,应该是我机器学习懂得不多,不少名词也就只知道名词罢了,而且不懂后置的Topological Data Analysis的操作,还是先看点正统数学物理再看看这个吧。
2025-09-12
经过晨哥的提醒,今天对6月23日的日记进行了修改,重新仔细论述了一下不可定向弦的世界面。详情请移步至六月日记。
另外,今日彻底完成了pure spinor介绍报告的ppt制作,后面就是每天准备一下讲稿了。不得不说写ppt真的是体力活,特别是我这种对格式要求非常变态的“强迫症”,除非是一些非常复杂的图片,其它学术上的图片必须要求是矢量图,所以做ppt又重新训练了一下我的Adobe illustrator水平。这玩意儿在写完毕业论文之后就没碰过了。这些病态的格式要求也使得我ppt写的非常缓慢,基本上每天只写一面ppt。所以还是beamer好,不需要搞那么花里胡哨的,就直接把公式和要点网上一摆就好了,而且我觉得这种简介排版也很好看的。
另外今天和友人谈到ppt制作细节问题,我戏言因为自己英语口语不行,所以除了前面用power point制作的warm-up,后面的技术内容全是用beamer写的,而且基本上就是要讲什么话原封不动直接放在beamer上面。说到其实我这是受Witten的启发,Witten的ppt也是上面一堆文字😂😂😂,说起来高能人还是完全不在意ppt格式问题,只要能看就行。反观本科一些老师,反复在无关紧要的ppt的格式上浪费时间,反复强调上面不能放一堆文字,要重视图表的堆砌。。。。。
2025-09-13
今晚整理藏于珠海家中的书籍,翻找到一本钱学森先生所著《星际航行概论》,当初高考完的暑假买的,可惜当时不太懂,买的还是盗版。对火箭原理之类的兴趣是玩坎巴拉太空计划所培养的,不过后来也废了这一爱好,就应用物理来说我目前对航天器轨道测算以及磁流体力学(等离子体方面)这些比较感兴趣,这里mark一下,希望后面哪天有机会继续看看这方面的书(万一能找到教职这就是我在上力学或者电磁学的时候能注入的特色内容😂😂😂)。
2025-09-14
今日在网站拓扑序讲义的最后一个part,一维拓扑序后面写了个注解,正式宣布这个笔记烂尾,不过网站上烂尾的笔记很多的,这很正常。我发现写笔记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一是如果你是学习笔记,那么给陌生人读起来也没有太多的参考价值,甚至会产生误导。二是就算是写给你自己的,但有写笔记习惯的各位扪心自问一下,有多少人最后会看哪怕一眼?所以可以看到网站上的笔记没有烂尾的那么寥寥数篇,要么是作为讨论班的讲义,要么是我最近至少长达半年的研究方向,比如CHY的笔记,这个笔记确实帮了我很多,我很多振幅的技术都是在学这个的过程中精进的,在我暑研期间也用这个笔记回顾了不少。特别是后面读博也没太多心思天天琢磨一些基础内容,所以网站上大概率不会频繁更新笔记,我认为真正对读者或许有一些帮助的解说记事应当是对自己专业领域或者本来就懂一些的内容的一些个人总结。比如我那个莫尔斯理论的帖子,就是在我本身就学过一遍,后面看网课又学了另外的思路,然后自己写了一个大致的证明思路(当然没烂尾的原因也是当初是准备用在一个数学系的讨论班上,不过后来还是没有在讨论班上讲)。
2025-09-15
今天终于看完了全部出口仁老师的《大家的日本语》初级的所有五十课文法解说视频,后面再花个四五天应该就彻底学完了这套教材。来珠海后基本都在赶日语学习落下的进度,没怎么学数学物理,不过在家这么久确实有点懒了,快点开学治一下我的懒惰。
另外学完初级也意味着差不多学完了动词变化,所以大致整理了一下动词活用(字体是随便找的一个可爱的手写体HuiFont):

2025-09-17
今日画完了所有暑期学校陈一鸣老师讲座笔记上的相关图片,把整个暑期学校的笔记先放在了网上。其实有很多内容没有补,特别是不少讲座听到最后一节课就慢慢跟不上了。而且回家之后入学事项以及纯旋量超弦介绍的ppt这些事情忙着就耽搁了。目前应该是不打算补了,我在上面都放了相应的参考文献供读者参考。关于张欣宇老师的讲座,正如我在帖子里面所述,因为这或许称为我博士期间的研究方向,所以我打算在自己懂了不少之后单独写一个解说记事。
2025-09-18
涉及到大量重复运算需要调用多次函数的时候可以先全部算一次然后每次计算的结果存储起来,也就是使用Memorization的编程思想。这个算法在mma里面的实现如下
(*无记忆化的斐波那契函数-效率极低*)
FibonacciNaive[n_] :=
If[n <= 1, n, FibonacciNaive[n - 1] + FibonacciNaive[n - 2]];
(*使用记忆化的斐波那契函数-高效*)
FibonacciMemoized[n_] :=
FibonacciMemoized[n] =
If[n <= 1, n, FibonacciMemoized[n - 1] + FibonacciMemoized[n - 2]];
(*测试*)
Timing[FibonacciNaive[30]]
Timing[FibonacciMemoized[200]]
输出为
Out[1]= {1.78125, 832040}
Out[2]= {0., 280571172992510140037611932413038677189525}
这个方法是我今天想去实现一维AKLT模型的能谱求解的时候学到的,来自于Hosho Katsura教授的MMA文件。比如可以用下面的MMA代码迅速给出哈密顿量的稀疏矩阵:
(*Pauli matrices*)
sig[3] = {{1, 0, 0}, {0, 0, 0}, {0, 0, -1}} // N // SparseArray;
sig[2] = {{0, 1, 0}, {1, 0, 1}, {0, 1, 0}}/Sqrt[2] // N // SparseArray;
sig[1] = {{0, -I, 0}, {I, 0, -I}, {0, I, 0}}/Sqrt[2] // N // SparseArray;
sig[0] = IdentityMatrix[3] // N // SparseArray;
(*Hamiltonian*)
(*OBC Hamiltonian*)
(*Memoriztion to avoid duplicate computation of Hamiltonian*)
Htrivial[leng_] := Htrivial[leng] = Module[{Sigz},
(*Spin operator sig along with z axe act on the site i=1,2,...,l*)
Sigz[i_] :=
(*Memorization*)
Sigz[i] =
Apply[KroneckerProduct,
Join[Table[sig[0], {l, 1, i - 1}], {sig[3]},
Table[sig[0], {l, i + 1, leng}]]];
(*Construct the Hamiltonian*)
Sum[
Sigz[i] . Sigz[i], {i, 1, leng - 1}
]
]
HAKLT[leng_] := HAKLT[leng] = Module[{Sig, Adjop},
(*Spin operator sig[a],a=1,2,3, act on the site i=1,2,...,l*)
Sig[a_, i_] :=
Sig[a, i] =
Apply[KroneckerProduct,
Join[Table[sig[0], {l, 1, i - 1}], {sig[a]},
Table[sig[0], {l, i + 1, leng}]]];
(*adjacent interaction operator*)
Adjop[a_, i_] :=
Adjop[a, i] = Sig[a, i] . Sig[a, i + 1];
(*Construct the Hamiltonian*)
Sum[
Sum[Adjop[a, i] + 1/3 Adjop[a, i] . Adjop[a, i], {a, 1, 3}], {i,
1, leng - 1}]
]
(*PBC Hamiltonian*)
PHtrivial[leng_] := PHtrivial[leng] = Module[{Sigz},
Sigz[i_] :=
Sigz[i] =
Apply[KroneckerProduct,
Join[Table[sig[0], {l, 1, i - 1}], {sig[3]},
Table[sig[0], {l, i + 1, leng}]]];
Sum[
Sigz[i] . Sigz[i], {i, 1, leng - 1}
] + Sigz[leng] . Sigz[leng]
]
PHAKLT[leng_] := PHAKLT[leng] = Module[{Sig, Adjop},
Sig[a_, i_] :=
Sig[a, i] =
Apply[KroneckerProduct,
Join[Table[sig[0], {l, 1, i - 1}], {sig[a]},
Table[sig[0], {l, i + 1, leng}]]];
Adjop[a_, i_] :=
Adjop[a, i] = Sig[a, i] . Sig[a, i + 1];
Sum[
Sum[Adjop[a, i] + 1/3 Adjop[a, i] . Adjop[a, i], {a, 1, 3}], {i,
1, leng - 1}
] + Sum[
Sig[a, 1] . Sig[a, leng] +
1/3 Sig[a, 1] . Sig[a, leng] . Sig[a, 1] . Sig[a, leng], {a, 1,
3}]
]
(*Total Hamiltonian*)
Ham[s_, leng_] := s*HAKLT[leng] + (1 - s)*Htrivial[leng];
PHam[s_, leng_] := s*PHAKLT[leng] + (1 - s)*PHtrivial[leng];
HAKLT是一个有能隙的系统,对于Haldane相,而trivial相也是有能隙的,我希望通过计算两者的线性混合之后的系统的能隙,说明在中间是存在一个无能隙的点的,所以就说明这两个相之间是不同的,是存在相变的。当然这只是一个非常初步的讨论,Haldane相是一个SPT相,所以在不考虑对称性的时候依旧是trivial的。这个后面我再写一个想法来论述。
我昨天一整个晚上大致就在纠结如何计算能隙,我用自己的方法最多算到$L=5$,但是我看网上轻松是$L=6$往上走。今天白天大致是搞明白了我需要用Memorization来防止重复计算张量积,用这个方法的极限就能比较轻松构建$L=12$的时候的哈密顿量(1个G的稀疏矩阵)。但是依旧无法直接计算能隙,最多算到$L=9$。所以我还不太懂有没有什么算法能高效计算能隙。
先贴个$L=8$的结果,因为我发现再往上走电脑就罢工了。不过计算得到的图像也能说明我想说明的问题了,而且定性上看图像和$L$更大的时候是一致的。
周期性边界条件:
L = 8;
sValues = Range[0, 1, 0.05];
Pdata = ParallelTable[
Quiet[PGap[s, leng]], {s, 0, 1, 0.05}, {leng, 4, L, 1}];
Pplots = ListPlot[Transpose[{sValues, #}] & /@ Transpose[Pdata],
PlotMarkers -> Automatic,
PlotLegends -> Map["L = " <> ToString[#] &, Range[4, L]],
AxesLabel -> {"s", "PGap"},(*将点用线连接*)
PlotStyle -> ColorData[97, "ColorList"]]
输出图像:
开放边界条件:
data = ParallelTable[
Quiet[Gap[s, leng]], {s, 0, 1, 0.05}, {leng, 4, L, 1}];
plots = ListPlot[Transpose[{sValues, #}] & /@ Transpose[data],
PlotMarkers -> Automatic,
PlotLegends -> Map["L = " <> ToString[#] &, Range[4, L]],
AxesLabel -> {"s", "Gap"},(*将点用线连接*)
PlotStyle -> ColorData[97, "ColorList"]]
输出图像(这个无所谓,可以看到和周期性边界条件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大家一般提到一维体系都是讲PBC或者无限长的链。一维体系加PBC是通过变$S^1$拓扑得到的,二维的情况下并非$T^2$拓扑,一种可行的方法是用Fuzzy Sphere。):
我这个计算方法是非常低效的,上面的代码要跑十分钟。我的想法就是很朴素完全对角化后看本征值最小两个的差值。而完全对角化对于大的稀疏矩阵几乎不可能。肯定有更简单的直接计算gap的方法,只需要部分对角化直到最小的两个本征值。不过我还不知道。似乎Arnoldi方法能做,但是我不知道为何还是很慢而且也会爆内存。而且Arnoldi默认收敛到绝对值最大或最小的本征值(算最大本征值还是非常快的,而且$L=12$也不会爆内存),和我想要的还是有差别。回头问问凝聚态人。
2025-09-21
今天更新了一下网站,push了一些文件并且更改了网站头像,另外就是我一直想改的favicon。我发现我借的别人的这个网站遗留下来的favicon并非注释中的16x16和32x32,所以我直接改了head.html里面的这段代码:
<!-- Icons -->
<!-- 16x16 -->
<link rel="shortcut icon" href="https://whuzbf.github.io/favicon.ico">
<!-- 32x32 -->
<link rel="shortcut icon" href="https://whuzbf.github.io/favicon.png">
到
<!-- Icons -->
<!-- 16x16 -->
<link rel="shortcut icon" href="https://whuzbf.github.io/favicon-16.png">
<!-- 32x32 -->
<link rel="shortcut icon" href="https://whuzbf.github.io/favicon-32.png">
原先的favicon我直接扔了,github会帮我记住。
等后面换电脑了接着契机想把老旧的3.0+(好像是2.0+,有点忘了)的Jekyll彻底升级成最近版本,不过可能要动很多代码。
9月23日抵达东京羽田机场并住在千叶柏
2025-09-23
“刚到东京,不熟地方”
今天坐机场快线没注意看站台,mud同一条线不同站台停车点都不一样,Google叫我到站不用换乘继续坐,结果到站他往反方向走了😂😂😂。车厢内一来日本工作的欧美老哥看我迷惑好心给我解释了,还怕我听不懂用deepseek翻译成中文。然后后面换乘铁路又给搞错了,站错站台目送要乘的车两次。连着问路人N次「柏行きますか」后终于到了柏,晚上吃饭还好有学长陪着,连着说一堆敬语也不知道他在说啥🤣🤣🤣
9月24日至9月27日在群马县草津温泉开party
2025-09-24
今天是温泉之旅的第一天,不得不说温泉的源头那里是真的臭,就像是老天爷放了一个巨大的屁。
今天也是我学术报告首秀,有点失败,时间没有控制好,后面大家都听累了,在家里自己讲的时候还行,但是后面Yamazaki问了我不少技术性细节的问题我没有解释到位让他比较困惑,所以浪费了不少时间🥹🥹🥹。
2025-09-25
报告听不太懂,不过今天晚上温泉倒是泡爽了。不过也没有那么爽,总感觉和浴池里面的感觉差不多,只是有一股硫磺的味道让你知道泡的是温泉罢了。
2025-09-26
今日听苗原学长讲了点 (spin)-Calogero-Sutherland,以及其Freezing极限Haldane-Shastry模型。听了这些天报告终于来了个讲的模型算是量子力学而不是量子场论的了。后面涉及到苗学长自己工作的时候我没听太懂,不过前面涉及到从Yangian的quantum determinant微扰展开直接emerge得到CS模型的哈密顿量倒是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直接了当地就说明了这个模型的可积可解性。不过这方面我的了解还相当粗浅,还需要后面好好和Yamazaki学学可积性。
这种可积的量子力学模型真的非常奇妙,我之前本科的时候曾经看过一些有关Calogero-Sutherland模型的相关内容,不过没有涉及到Yangian这些。听这个报告有不少亲切感。
晚上和Yamazaki聊为啥pure spinor的计算无法计算机自动化,和晨哥聊了之后我觉得第一是CFT不是自由的,这增加了计算复杂度;第二是计算过程中需要很多人为操作化简表达式,而这种化简可以用很多不同的relations去化简,显然这是一种艺术,目前的编程还无法完全做到。不过这让我想起来去年暑假Cheung和Schwartz尝试用人工智能化简纯旋量超弦表达式(2408.04720)。不过我看效果并不好,而且何老师也批评这个工作其实很trivial,根本不需要用AI去化简,完全带不来任何新的物理或者更好的表达式。
另外Yamazaki也和我讲了一个巧合,我们说弦论是UV不发散的,但我们同时也需要注意到IR发散。在QFT里面我们可以说IR发散只是我们定义散射振幅时候的subtle,我们可以用软定理去抵消掉IR发散。Mandalstam在很久之前在光锥坐标下证明过弦论的IR发散也是可以被抵消的,而Berkovits,作为Mandalstam的学生则使用了pure spinor在无需假设光锥规范的前提下证明了这一点。(当然这里我和Yamazaki只是随口一聊,不保证这个故事的正确性,我也懒得查相关的文献了,就先放在这里)
2025-09-27
今日听佳康学长讲报告,太难,完全听不懂,甚疲。希望过个两三年我能开始做一些这么难的数学物理科研,我还是先干一点简单的吧。
9月28日至9月30日在东京旅游
2025-09-28
今天去浅草寺玩了玩,中午两点出去晚上五六点回来的,但实际上也就在那里呆了四十分钟,因为我又坐错了电车。原来如果进错口了得找车站工作人员帮忙,日本电车是不能同一个车站进和出的。
在浅草寺花三千块买了个御朱印帳,这就相当于通关文牒了,希望日本读书这几年不光对物理问题思考得更加清楚,也能多出去走走,把通关文牒每一页都打上朱印。
2025-09-29
今天第一次去东大,因为要选工位,有一个靠窗的风景特别好的位置,不过感觉大家都会选,希望我能运气爆棚抽中。第二志愿的工位就平平无奇了,不过好在和watanabe在一个办公室,所以我可以多和他聊聊。
然后早上去了根津神社,发现朱印只能打印不是直接手写在御朱印帳上的,隧反。不过他有个低配版的千鸟居,还不错的,希望之后在京都去个最屌的。
中午再去了相邻的另一个神社,湯島天滿宮,听说供奉的是菅原道真公,类似中国文殊菩萨,这得求一下,求一手科研顺利。
下午去了神保町,这里的书店果然是名不虚传,去明倫館买了两本SGC出品的弦论和M理论的书,因为纸质版本都已经停止印刷了,这里卖的都是旧书,所以还比较贵,七千块钱拿下两本,还在可接受范围内(听说东大内部有专门卖数理科学杂志的地方,之后去看看,据说学生卡九折,相当于免交百分之十的税了)。日本这边基本上轻小说漫画之类的新书一千可以拿下,文学之类的可能就要两三千了,理工的SGC这种算很便宜的,两三千可以拿下,精装本比较贵的可能需要五六千。不过感觉洋文原版书在日本也不是太贵,也是七八千。不过可能是我看的那几本不贵,之后常来书店逛逛。(或许每个月可以留下一万买点书看看)。
2025-09-30
今天打算push笔记,有一个问题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解决,就是网站上涉及到代码块的时候,liquid会自动将其解析,可能会出现语法冲突,隧问deepseek,告诉我可以用liquid的raw环境包裹起来。所以可以在尝试报错或者报警的地方用这个环境包裹一下(虽然治标不治本)。